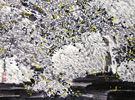二零一零年六月一日,日本的摄影之日。我带着荒木经惟最喜爱的威士忌来到了下北泽。在一起前往酒吧途中路经另一家小酒馆,「主人在睡觉,不过我进去一下」,荒木经惟将他刚拿到台湾出版的《走在东京》,翻到拍有这家酒馆的照片那页,放在桌上:「他应该会吓一跳吧,哈哈哈」……。
黄亚纪:我经常来到日本,近年来日本社会各方面面临着转换期,其中一个特性就是女性变得强势了。不知就一个摄影家而言,您对这些变化有怎样的想法?另外,未来的日本女性像会是如何呢?
荒木精惟:(荒木将女性Zyosei和情势Zyou-sei有些听错),情势不可能预测的吧,波波波,乱七八糟的吧。政经情势?会怎样呢?应该一路下坡吧?直到天昏地暗吧?无药可救吧?但是,我相信这不只是日本,不只是东京喔。虽然台湾的情势我完全不了解。
啊?什么?是问女性啊?如果是女性的话,女人应该一路变强吧,一定是女人比较强的,我从一开始就这么认为。女人是在上面的喔。而现在这已成事实了。「比起男人,我们更为优秀!」,现在女人不是都敢这样露骨的说了嘛,之前还稍稍控制自己,谦虚不说呢,哈哈哈。
黄:您一向以女性做为拍摄对象,通过这样的女性像,您最终希望表现的是什么呢?
荒木:虽然有「表现」这样的词汇,但事实上我并没有表现,在表现的是女性、是女人、是被摄体,而我只是将他们复写出来而已。如果要用「表现」这个字啊,不如用「表出」,也就是诱发出来,女性其实怀着希望被诱发出来的欲望呢。
但是就像我刚才所说,现在已经是女性不需要诱发,就完全显露出来的时代啦,所以已经不需要我啦,女人们啊「喀~」地显露出来啦,知道吗,要接受也是很辛苦的事呢,哈哈哈。
比如说,以前我说,相机就是男性性器,但是最近,我反而觉得是女性性器了呢,相机啊,是受容、是接受,最近的我是如此感觉的。但是就在这时候,我得了点癌症、身体状况不大好,所以现在,相机是棺材呢,我把大家都放到棺材里面,哈哈哈。所以变成了这副德性。
年轻的时候(相机)是攻击性的男性性器,而现在变成女性性器、是接受的时期了。只要我拿着相机,很自然地、不知不觉地就如此感觉呢。但是,已经接受太多,装不下了、吃不消了,哈哈哈。
黄:从什么时候有这样的改变呢?
荒木:嗯,稍早之前吧,啊,或许是更早之前吧(笑),要我说这个事情不是让我很恼怒吗!
但是我一边一直说着棺材,一边拍照,结果,你看,Chiro就这样死掉了呢……。还真是有趣啊……(面露哀伤)。
但是呢,现在我在拍的就是「Chiro死后」呢,小Chiro死了以后,荒木会变成怎样呢?或许你会说,大概就是又拍着天空吧,如果你这样想,那你就错啦,我还要、还要拍呢。
猫啊,似乎能够了解每一个人呢,无论是你说的话或是关于你的所有事情。
但是我啊,最近总是被谈到癌症的话题,我已经累了。换我来问你好了:如何?你有得癌症吗?是不是得了乳癌了?我可是很会帮人找乳癌的喔,哈哈哈。
现在真的很流行癌症啊,果真是时代的疾病……。
黄:您提到拍摄天空,就我所知,您因为所爱的对象不在了,所以拍摄天空,拍摄「虚」。
荒木:我不只是被摄体死亡时才拍,我一直拍摄着天空。虽然我不信佛教那一套,但是天空真的有着什么呢。你想想,当你所爱的人去世时,你为了不让眼泪留下而头往上仰,那不就望着天空了嘛,哈哈哈。
天空,不曾停止变化。虽然天空飘着云彩,但从未有一刻是相同的:时刻变化,朝着变化而去。说实话,就我的个性而言,我其实很讨厌按下快门、把事物静止下来、那所谓的「摄影行为」呢,我其实很希望能够「咻~」地不断变化,所以我才会被「动」的东西所吸引吧。
天空,你看,是「空」吧,所谓的空虚,虽然这是佛教说法,但我所说的空、我所拍摄下来的天空,并不是宗教的空虚:「天空非空」,天空不是空虚、不是空无一物。具体来说,天空包含着各式各样的东西,但既不是抽象的、也不是精神的、又不是「悟」、也不是「禅」,而是具体的、是心情的具象化,不是吗?
天空是从自己心情的流动而形成的东西呢。以前我最常拿来比喻的就是,天空就是一扇窗户,只是现在我老爱装模作样,改口说那是底片(film),但是其实只有天空才是拍下心情的底片呢。不过那些用数字拍照的人,可是真的什么也没拍下,不行的啦,哈哈哈。
很难理解吧,我光是随意说说就说成这样,哈哈哈,因为我已经是神了啊。
在这之前不久,我还在天空的照片上作画呢,说那是我的「遗作」,你看,摄影是谎言吧,我可是到现在还活着呢,对吧,哈。不过,和天空相对、或是对决、或是合作,或许就是因为这样,因为做了这些事情,所以我才又得到了生命呢,我是这么想的。我们(摄影家)啊,只有继续拍照才能活下去呢,所以怎样都好呢,我可是什么都拍啊,不只是天空。
黄:在东京,从家里阳台上可以看到天空,真的很棒呢。
荒木:对,我称我家的阳台为乐园,那可是Chiro的最爱,可惜现在她不在了,已经是废园了呢。我现在很后悔呢。还有我的寿命,大概还有一年半吧,我的寿命。
所以,事物无常,什么重新制作、整修,像是法隆寺的整修等等,那可是不行的。因为所谓的时代,就是注定要被风化的,注定要与崩坏有所交集,人类也是一样啊,所以希望什么返老还童、希望看起来更年轻,不可以这样想喔,万物都必须和自己的年纪相应,只要有那个岁数应有的魅力,那就足够了。如果脸上长了皱纹,也有皱纹的美丽,反而是没有了皱纹,才会变得无趣呢。云也一样,如果没了细节,那就非常无趣。
所以,比起画面的空间细节,我更喜欢像是时间的细节的东西呢,摄影若能传达出那个时候、那个年代、那个年龄的感觉,那就好了。或许用「时代」是过于粗略的,但是真是如此,因为我们来到的,就是时代的此时此刻,不是吗?
黄:那您对于历史、过去的看法呢?
荒木:我是为了自己而活,也是为了活着这件事情而拍照,所以,对于历史、传统,我是没有多大的兴趣。因为,每一天、每一刻,都有属于那天、那刻的欢乐,不是吗?
黄:那你有没有希望被生在不同的时代呢?比如说没有相机的时代?会不会无聊呢
荒木:是啊,没有相机!那可不行呢。
黄:那数位时代呢?你有什么想法?
荒木:已经结束了,我根本不想把数字纳入摄影的范围里。尽管听起来像是玩笑话,但我可是认真的:我最大的秘密,就是我对摄影的感情,其实是「不暴露」。所谓的数字,是极端的、直接的、暴露出来的、并且是太过暴露的。所以,数字不是很无趣吗?全都暴露了,没有意思的。摄影,就像是拥有越多秘密的女人,越有魅力,哈哈哈。
日本的富士底片,到了现在还执着生产底片型相机,甚至还推出6x7蛇腹相机,根本是卖不了的东西,却刻意努力坚持,这和我现在的思考是相同的呢。
所谓的底片型相机,在操作上有些麻烦的地方,所以到拍摄前需要一点时间,而我认为这点时间的感觉,就是摄影成为摄影的感觉,这才是真正的「直接(straight)」。这和什么光线与相机的平衡啊、决定的瞬间啊,一点关系也没有,只是单单的「拍摄」而已。事实上,这反而像是数字在做的事呢。这才是真正的摄影啊,所以我才这么做。
黄:那您对于摄影的想法也因此改变了吗?
荒木:我对于摄影的感觉,自始至今,未曾改变。今天有粉丝拿着我以前的摄影集来给我签名,当我看那些照片,发现即使到了现在仍没有任何改变。这次我在Taka Ishii画廊展示了「古稀的摄影」,并不是我摄影的顶点,而是和最初一模一样的摄影。我又重新开始了喔。和最初相同的摄影。果然,我还是要坚持底片呢,虽然我很讨厌这么说。
「古稀的摄影」,真的和我最初拿着相机、按下快门的心情,是一模一样的。有人会问我,「你这次怎么了?完全没有表现啊」,如果你没有仔细思考,是不会了解这些摄影其实是很棒呢。
从「古稀的摄影」开始,也就是说「摄影七十才开始」啊,我要打起精神,对手是毕加索和北斋,所以我得活到九十岁、一百岁、继续拍照,不过大概在那之前我就会被神给带走吧,哈哈哈。
黄:您提到毕加索、北斋,想请问您,您认为只有天才才能创造杰作吗?
荒木:嗯,艺术是努力不来的,从一开始就被决定的喔,看看艺术之神是不是站在你这边。我是这么觉得的,艺术是一种诈欺,不是学历。
黄:最后我想请问,现在世界各地流传着二零一二年世界毁灭的预言,如果二零一二年人类果真要灭亡了,您最后想要拍下什么照片呢?
荒木:到了那时候啊,就是那时候经常相遇的女性吧,或许是一只小野猫,或许是骑着脚踏车经过的母亲和小孩。当下那时刻所相遇的事物,就是我摄影的本质,「想要拍下的照片」?从来没有过的。
从开始到现在,我与不同的相遇交会:母亲的死、父亲的死,当然也不是只有死亡,还有和阳子的相遇、和Chiro二十年来的交往,这些不都是人生的相遇吗?
所以我想,一定的,在人类灭亡的时候,会有美好的相遇存在。
感谢东京Zeit-Foto Salon的石原悦郎先生与铃木利佳小姐对此次采访的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