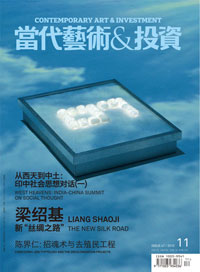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当代艺术”何时陷落到集体性的焦虑症状中?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
如果反复回看过去三十年中不同的艺术历史阶段中的历史事件、个案、和代表性的艺术作品,这种“焦虑”可能被转化为一种“阴影”至今尚未解脱,反随着国势上升而愈演愈烈。
1980年代强调的“启蒙”和“解放”是以西方为标准的,这个西方显然是作为中心的欧美,而非其他。80年代剧烈的艺术革新潮流并未使中国艺术获得某种程度的解放,而是更深的卷入了对西方的想象、期待和被西方命名的焦虑中,事实上,80年代中国艺术从未有机会走出国门,参与到与西方的对话与讨论中,此种现实也是话题的关键。
如果我们以1989巴黎蓬皮杜中心举办的、划时代的展览“大地魔术师”获选参展的三位艺术家黄永砯、杨诘苍和顾德新作为80年代艺术的“终结”,展览中的西方艺术家和非西方艺术家并列展出,也不意外着中国获得了某种参与构建西方(世界)历史的机缘,策展人马尔丹在策划前言里明确写道:“艺术家在这里作为出自他们文化元素的个体被介绍,而不是作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代表。”
今天,有的艺术家会坚持自己的“中国”身份;有的艺术家则会明确忽略国族身份概念,而标榜自己是世界主义的、全球化的;当然也会有第三种艺术家的出现,拒绝进行艺术创作或拒绝成为艺术家成为一种“新”的艺术观念,没有身份之争,只有立场。
2000年在中国本土发生的上海双年展,不仅意味着官方对本土当代艺术的解禁,也说明要即刻参与到全球艺术对话的潮流和现实处境的迫切性。此次展览中,西方艺术家、中国艺术家、和处在“第三空间”的艺术家共同搭建了艺术对话的平台,展览主题则是强调一种精神,上海作为20世纪最早的国际化的中国城市象征的复活。
之后的十年中,在内地越来越多城市涌现的双/三年展也在照搬这样的组织、策划的内在对话逻辑,策划团队中的跨国界成员的构成成为一种标准、信号和正确性。但是回到话题的起点,西方艺术(艺术家和策划人)对中国艺术的介入和交流过程,并未丝毫改变“中体西用”的思维惯性。
2010年上海双年展,我想提醒观众和读者注意的是,双年展项目的第五部分“从西天到中土:印度中国学者高峰对话”,《当代艺术与投资》计划对此项目专题讨论和专文发表。
涉及到前面部分谈到的西、中问题,和如何转化?命名?和建立新的主体想象时,我想转述项目策划人之一陈光兴教授所谈到的:“必须在民族国家内部的本土主义与欧美中心的世界主义,此两者之外,寻求新的参照体系。”这是一种思维和工作的必然,也是现实最为迫切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