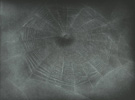1912年,“不祥之作”《亚维农少女》在巴黎艺术圈引起的轩然大波尚未消散,毕加索便已开始思考下一个问题:艺术将往何处去?
对当时的艺术家而言,20世纪初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日趋成熟的摄影技术令写实绘画相形见绌,社会、科学、宗教、政治均呈现出新旧交替的局面,“现实”的定义正在被改写。纷乱的色块组合、极端的单平面形式、多视点的构图法、斧凿般的生硬线条、散发出危险气息的性感裸女……横空出世的《亚维农少女》无疑是那个年代最具代表性的新面孔之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幅立体主义的开山之作也是毕加索给欧洲传统文化、审美旨趣与理想主义的一记响亮耳光。
自此,毕加索对立体主义的热情一发不可收。在挚友乔治斯·布拉克(Georges Braque)的启发下,他开始从人物肖像转向静物画,尝试更激进、更抽象的表达方式。这一实验仅维持了短短两年时间,却是现代史上最激烈、最著名的艺术革命之一。
上周日,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举行的回顾展《毕加索之吉他:1912-1914》,即是对这一历史时刻的探索与追问。
早期立体主义
本次展出的70余件作品包括来自35个公共及私人收藏的油画、素描、照片、拼贴画及结构作品,其中两座“吉他雕塑”是在毕加索辞世后首次公开亮相。从早期作品中可以看出,毕加索的自我定位依然是“立于传统艺术金字塔尖的画家”。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是1912年问世的《瓶、吉他与管道》,你可以在它身上找到拼贴画的所有经典元素:剪切、雕刻、粘贴等多道工序营造出的立体感、凸起的贴片在画面上投下的微弱阴影。实际上,这是一幅纯以笔墨造就的“伪拼贴画”。
诞生于同年秋季的《吉他、乐谱与酒杯》则是一幅货真价实的拼贴之作,它由剪报、乐谱与仿木纹纸组合而成,当中贴着一幅小型油画。相比于严丝合缝的构图形式,毕加索似乎对各种稀奇古怪的几何图形更感兴趣,其创作手法可用大巧若拙来形容。他热衷于用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来组合或包装生活中最常见的静物元素:高脚杯、咖啡杯、酒瓶、乐器等等。这些道具在挤满落魄艺术家的廉价酒吧与咖啡馆中俯拾即是,它们是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却在毕加索笔下折射出另一个现实维度。
早期的立体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全新的绘画流派,倒不如说是一次试图重新定义“艺术”与“现实”的尝试,依然是与现实世界血脉相连的半抽象艺术。那时候的毕加索似乎并不打算走得太远,他钟情于圆柱体、半球体等单纯的几何学形态,用半抽象艺术形式来取代光色分析,但仍注重视觉的观察与描摹,而非突破一切束缚的自由创作。
激进实验
如果说早期立体主义依然是与现实世界血脉相连的半抽象艺术的话,那么毕加索后期展开的激进实验可称得上是公然与传统叫板的另立门户之举。在诞生于1913年3月31日的拼贴画《吉他》中,我们已无法找到任何与油画有关的痕迹。以映射自然物为宗旨的现实主义色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立体主义的“别样真实”。在许多奇形怪状的贴片当中,我们似乎可以窥见一把吉他的影子——没有形体,没有深度,没有一丝与现实接轨的迹象,恍若鬼影一般。
此后,毕加索又“变本加厉”地用纸板和细绳打造出一座吉他雕塑。作品照片经《巴黎莱斯文科学报》登出后,愤怒的来信如雪片般“纷涌而至”,一些读者甚至因此取消了对该报的订阅。这件“大逆不道”的作品如今已成为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头号展品,其大小与真正的吉他不相上下,看上去有一种令人心悸的脆弱感——它从未奏出过一个音符,却在一刻不停地向每一位来访者提问:什么是真实?为何一种真实会胜过另一种?为何永恒胜过瞬间?什么是高?什么是低?是什么造就了物象,又是什么褫夺了思想?
或许正因如此,毕加索的“纸吉他”被评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雕塑作品之一。然而毕加索本人始终拒绝公开展示这件得意之作,直到他1973年辞世后,吉他雕塑归现代艺术博物馆所有,才有机会重见天日。
毕加索的激进实验走得比人们想象中更远,然而作为一位天生的人物画家,他从未尝试过从具象到抽象的“自由落体”。尽管在1913年的《头脑》中他曾无限接近这一可能:黑色背景中凸现出近乎虚无的空白,一对细微的小黑点依稀可见。事实上,如果不是因为这最后一刻的“点睛”之笔,毕加索或许会完成一次足以改写当代艺术史的华丽蜕变,甚至有可能与后来的胡安·格里斯一起成为综合立体主义的奠基人。
然而,冥冥中似乎有一种强大的惯性将这位天才画家拉回“正轨”。1914年以后,充满肉感的裸女、长袍曳地的少妇、构图严谨的人物肖像重新成为其笔下主角。那个狂放不羁而又细腻逼真的平行世界如火花般稍纵即逝,却足以构成毕加索创作生涯中最令人惊艳的篇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