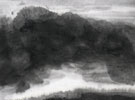海涅讲过一个故事,小提琴家沙洛蒙斯教英王乔治三世拉琴,对他说:“提琴家分成三等:凡是根本不会奏琴的,算第一等;奏得很坏的,算第二等;技艺高超的,算第三等。我王陛下已经跃入第二等了。”这些为母亲画像的艺术家,究竟算哪一等?不管技巧如何,只要画过母亲,总归不会是末流。
每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天,商业机构反复提醒这天是母亲节,你总要准备点什么向妈妈表情达意。可1910年之前并没有母亲节这个提法,人们也很少送康乃馨或忘忧草给妈妈。然而在艺术家的一生中,并不缺乏对母亲的献礼。
艺术家的天分不仅仅表现在美化事物上,很多人把画母亲的任务完成得十分出色。丢勒在母亲去世前的两个月用炭条为她绘制了一幅肖像,画中人饱经风霜、青筋暴跳,却透露出慈爱和真情。那些善用光影和线条的画家巧妙地略微牺牲了一些美而保全了深情。母爱像一块硕大的磁石,将缪斯的门徒们吸引到母亲身边。
艺术史上最著名的母亲
艺术家的履历里很少提到母亲,或一笔带过,比如,莫奈的母亲是里昂人、爱德华·蒙克5岁时母亲死于肺结核、雷诺阿的母亲是一名专做女式连衣裙的裁缝。惠斯勒的履历也差点写成:离开美国到伦敦搞艺术后,他再也没见过寡居的母亲。
安娜·玛蒂妲·麦克尼尔是《黑与灰的一号编曲:艺术家母亲》的主角,也是艺术史上最有名的母亲。1866年,这位生长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淑女为了躲避内战,带着被翻到起毛的《圣经》扬帆来到风化和天气一样糟糕的伦敦,投奔儿子詹姆斯·阿博特·麦克尼尔·惠斯勒。
1871年,安娜67岁,因为被模特放鸽子,惠斯勒将脸皮起皱的母亲拉到画室里。安娜在写给姊妹的信中写道——他说:“母亲,我要你当我的模特,我早就想为你作画了。”
这是同住5年以来,安娜在儿子的画室待得最久的一次。当了几天模特之后,已经开始骨质疏松的她累得站不住了。惠斯勒放下画笔,为母亲搬来椅子和脚凳,然后,他退到几步之外,看到了梦寐以求的构图。他笔下的母亲虽是一身玄色,却是黑里掺了红和钴蓝的暖调子。整个画面是黑白灰的组合,色彩和构图都正合他的心意。
惠斯勒的本意是描绘母子心灵上的隔膜,但观众看到惠斯勒的母亲却想起自己亲爱的妈妈,甚至想拥抱她。后来,惠斯勒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幅真情流露的画。“自己的母亲总是得画漂亮些。”他假装不在乎地说。
1932年,美国人惠斯勒的“美国母亲”,漂洋过海回到美国展出,它长时间占据着报章的头条,在经济危机中挣扎求存的美国人虔诚地膜拜这位克勤克俭的母亲,她的清教徒美德都在感召着朝不保夕的美国人,告诉他们苦日子会过去,母亲永远在这里。
母亲即家园
惠斯勒虔诚的母亲并不孤独。尽管关于艺术家母亲的信息在他们的履历中总是无足轻重,可在艺术创作中,她们却是取之不竭的母题。通常,艺术家面对自己的母亲也比面对其他模特放松得多,潜意识里他们似乎总被母亲的爱或痛苦深深影响。
母亲“残破的容颜”深深地吸引了伦勃朗,他所画的母亲捧读《圣经》的画作,既表达了眷恋母亲的情怀,亦是一种宗教情结。伦勃朗的母亲入画时,已经在人生的最后一个季节,早已失去了女人的美丽。但一贯深思熟虑的伦勃朗,不讳言她的每一条皱纹、每一点苦难。他笔下的母亲虽然沉默又冷静,却有极深的感染力。
曾在法国南部同住的高更与梵高,都是对着照片描绘母亲。不知这是不是他们创作竞赛的一部分,两位潦倒艺术家笔下的母亲看起来都是那样不同寻常——高更把母亲改成阔鼻厚唇的西班牙人模样,梵高则给母亲画上淡绿的面孔与深绿的眼珠。将母亲异化,是他们爱而不得的结果。
美国20世纪最著名的抽象表现主义画家阿希尔·高尔基,一直无法忘记饿死在逃荒路上的母亲。当他从亚美尼亚逃到美国,在纽约作为艺术家展开工作时,首先画的就是一张他和母亲在1921年的合影。这张叫做《艺术家和他的母亲》的画上,阿希尔的母亲抿着双唇,全身紧绷地坐在椅子上。儿子阿希尔站在她身后,像只柔弱又好奇的小动物。
照片原本是寄给阿希尔远在美国的父亲的,好让他不要忘记家里的亲人,没想到竟成了阿希尔日后怀念母亲的凭据。他经历了惨绝人寰的亚美尼亚大屠杀,但却从未直接触及这一题材。只是这幅有母亲的画,阿希尔用了十多年不断地重画又涂改,就如同不愿承认母亲和家园已经离他而去。
一千位母亲有一千种情态
“与我的儿子在一起,没有一个女人会幸福。”知子莫若母,毕加索外貌和性格都与母亲十分相像,随心所欲描画各色女人。他的西班牙同乡格里斯·胡安把母亲画成立体主义作品,毕加索却不敢造次,毕恭毕敬将母亲画成庄重漂亮的贵妇人。在毕加索1923年为母亲所画的肖像里,玛丽亚·毕加索·洛佩斯一身玄色,侧身而坐,眼睛看都不看正在观察自己的儿子。
一千个人的母亲有一千种情态。法国印象派女画家博热·莫里索的母亲和妹妹坐在一起,画面充满了巴黎的闲趣和生活气息。纳比派画家爱德华·维亚尔的母亲和妹妹则在装饰性极强的墙壁和衣裙衬托下显得十分诙谐。乔治·修拉的母亲与他画中其他人一样,由无数圆点构成。亨利·奥赛瓦·丹拿的母亲则以一种东方情调的忧郁入画。亨利·德·图卢兹—洛特雷克的母亲是他的靠山和代言人,终生呵护着残疾的他。在洛特雷克笔下,饮茶的母亲安详可靠如圣母玛利亚。
相比起来,擅长摄影拼贴的英国画家大卫·霍克尼对母亲则表现出局外旁观的态度。1977年,他拍自己的父母亲坐在一个房间里;1982年,父亲葬礼当天,他拼贴的照片中的母亲坐在墓碑旁,穿着裹尸袋一样的雨衣,表情伤痛;1985年,母亲的脸被他组合成破碎的图案;1988年,他为走出丧夫之痛的母亲拍摄了一张温柔的肖像照。
也有人对为母亲画肖像这回事非常认真,照相术的追随者朱尔斯·巴斯蒂昂·勒帕热所绘的母亲肖像严格遵循写实原则。而安格尔的母亲则笼罩在柔和的侧光中,神情肖似岩间的圣母。动不动就大发雷霆的火暴的塞尚也一反常态地描绘起母亲做针线的温柔午后时光。为了不惹自己生气,他把角落里已经画好的父亲涂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