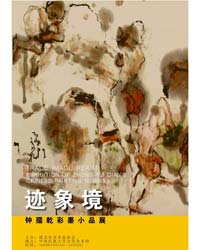李路明是中国消费现实主义时期“后波普”浪潮中具有独特意义的艺术家。作为一个参加过’85新潮运动的老革命家,他早年的活动主要是以幕后的推动者,即艺术批评家和艺术出版家的身份出现在中国当代艺术舞台上的。在这个方面,李路明为当代艺术做出了很独特的贡献。自89之后,思想界开始了失语的时期,从那时起,他才逐渐放下批评家的工作,除了继续从事艺术出版事业之外,逐渐以一个艺术家的身份,以他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艺术的创作。并且从一开始,李路明的创作关注的就是中国的消费现实状况。
李路明的作品对于中国消费现实的关注主要是从个人经验层面展开的。
到目前为止,李路明的作品主要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88、1989年开始是尝试性阶段,这个阶段的作品特点就是主观的理论判断过于明确,这是由于早期李路明批评家的身份和思维方式的影响,由于对艺术历史的研究很是清晰,所以使得他开始的艺术创作就直接进入了一个理论先行的道路。我们才知道为什么,从创作的初期,李路明就提出了一个“新形象”的概念。因为在那个阶段,作为一个理论研究者,他已经敏感地意识到中国在89之后社会的模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试图找到一个出发点来表达他对于那个时代压抑的内心感受和社会状况。这个时期的主要作品有《红树家族》系列(1988、1989年左右,油画)、《昨日种植计划》系列(1990-1991年,油画)、《今日种植计划》系列(1992-1995年,油画)、《96、97种植计划》系列(数码图像)、《种植躯体》系列(1998、1999年,油画),《红色日记》系列(2000年,布上印染)。在这几组作品中,我们看到他对于中国这个意识形态国家的矛盾态度。红树作为一种隐喻具有这样的倾向。这个时期的李路明主要是受到’85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没有摆脱想要创造新艺术样式的思路。这也是那个时期很多艺术家的主流思路,企图从风格层面上创造原创性的作品来完成自己的艺术使命。“新形象”的提出正是这样一种思想路线的结果。而那个时期,另外一批艺术家则更加深刻地理解了现实的中国情境,从而出现了后来某些批评家提出的“政治波普”和“玩世现实主义”艺术,以王广义、李山、余友涵、方力钧、岳敏君等艺术家为代表,这些艺术家的作品直接切入意识形态问题,而成为那个时期艺术新形象的不同代表,而李路明等艺术家从艺术的样式语言出发企图创造新艺术形象的实验由于远离了对现实中国主要文化针对点的关注,而被边缘化,没有能够被当时的批评界视为代表那个时期中国艺术新转折的趋势。这些作品只有历史现象学的研究意义,而缺少作为时代转折的历史导标性意义与价值。 我们今天看那些作品在思路和想法上,都还是过于简单,虽然他也感受到消费主义的某些影子,试图在作品中把握,但是那个时期社会的主要关注点仍然是意识形态问题。作为一个企图回避者,李路明对于消费问题的把握也同样的矛盾,这种矛盾在于消费问题在中国始终的都是在意识形态笼罩下发生的特殊问题,于是也混淆了人们的判断,人们将某些艺术家的“后波普”作品误读为“艳俗”,就是两种矛盾价值观共存现象造成的错觉。
李路明第二个阶段的创作从1995年开始,开辟了新的思路,即《中国手姿》系列对流行文化和消费文化的关注,从他创作这组作品的第一件《中国手姿NO.1》来看,他创作的初期作品的面貌与艳俗还是有很大的距离,但是由于当时中国消费现实还没有全面的展开,人们普遍地认为当时的消费是一种假象,艳俗在这样的背景中展开,也就将一些贴边的艺术家和作品归入了这个思潮。这件作品的黑白构成根本上讲是对自玩世以来的艺术样式和色彩感觉的背叛,可是到96、97年后这个系列的其他作品却使用了相对鲜艳的色彩,显然这个转变对于他来讲是矛盾的,我们也能够看到是当时“艳俗”艺术理论对于很多艺术家创作的影响。虽然在色彩上李路明的这些作品有着艳俗理论所描述的某些特征,但是在画面形象和他所传达的文化指向上,他是意图明确地指向消费现实问题的。那些女性的高跟鞋、手机、红五星都是那个消费主义兴起的时代被消费的对象,它们都是消费时代最日常化的物品,我们今天也还在消费这些东西,它是一种日常化的消费状况。而那些物品与一只被挪用并通过转换而变得性感的中国佛教手姿的结合,又使得这种消费现实主义的针对性更加明确。在消费主义时代,物质化图景社会的出现,首先是从女性的消费心理出发的。女性是消费主义社会的主宰,女性从本体上是享乐主义的,而享乐主义正是消费主义时代的特征。
李路明的第三个阶段的创作自2000年之后,这个时期他对于自己提出了新的要求,这种要求是基于他个人的经验之上的。他发现以前的创作,都只是试图找到新的造型形象,但是那种新的形象并不是出自于他个人的生命经验。于是李路明开始改变路线,不再关注新形象的问题。他从另外的一个方向开始思考自己的出路。终于,一个曾经困扰着他的问题得到了回答:别人的枪是能够用来打自己的仗的。他发现了里希特的某种语言是适合他自己要表达的东西与情感的。在那种被处理过的照片的背后,他感受到一种曾经让他魂牵梦绕的东西,那种东西就是他曾经的青春与记忆。艺术家虽然用了里希特的枪,可是那把枪在他的手上却被改变了打法,里希特让历史得到了拷贝式复活,而李路明则是重新借历史图像书写自我的青春幻觉。里希特的经验是一个时代的群体公共性的理性经验,李路明的叙述则是侧重于个体性的诗意体验。差异如此不同。这种不同我们可以通过比较里希特与李路明的《云上的日子》系列为代表的作品中找到根据。对于李路明来说,他不是在表达历史,而是他试图通过自我的故事叙述来重新体验被神圣化的“亚宗教”情结。这种“亚宗教”的情结能够使他在这个物质主义的、没有人能够再感到安全的社会中获得短暂的安全。
但是,这种安全感注定是暂时的、虚无的、幻觉的,也就是如同云上的日子。
我们身处在一个个人必须独自承受恐惧、焦虑和不平的时代。人们不会再把社会的恐惧、焦虑和不平积累成“共同的事业”,由全体人民共同去面对。毛的时代,人民之所以能够在一个物质普遍贫乏的社会中感受到安全可靠,在于那个时代别无选择的信仰和乌托邦化的军营式管理方式。这种方式在给所有的人提供相对平等的分配时,就一并将那种竞争性意识化解为一种休戚与共的立场。在那样的时代,个人立场与共同立场都遵循一元论原则,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属于哪一个阵营,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是一回事情。当我们一起去面对恐惧与灾难的时候,我们个人的焦虑消失了,时间的不确定性被群体性的信念所克服。而当今的世界,物质的繁荣使得个体的选择性成为自由的权力,但是这种自由的选择权力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安全与稳定。个体在选择自由权力的同时,也选择了必须独自去面对灾难、恐惧和焦虑。在这样一种状况下,我们再也不会知道第二天醒来时,我们属于哪一个阵营,于是,全体人民的“共同的利益”也就无法辨识了。问题是全体人民的“共同的利益”真的存在吗?
这种时代的转换是怎么发生的呢?李路明是否企图通过这样一种客观的个人叙述来反思历史的迷雾呢?
李路明所回味的是故事,是一幕幕以毛主义为宗教信仰的群众运动中普通人的生活场景。这种普通人的个体化的生活状态虽然也反映了人性化的一面,具有作为普通劳动者情感升华的效果,但是这种普通人的生活仍然是被淹没在一种“违反天性、违反常识、违反欢乐”的有效的毛主义的运动中的。因为任何有效的主义都是建立在群众自我牺牲精神的基础之上的,否则决不可能。而“自我牺牲精神往往是一种对现实认知有所不足的衍生物”(美国 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第二章)。任何一种主义都是让人去信仰的,而不是让人去理解的。对于参与到群众运动中来的狂热的人群来讲只有那种让他们不理解的东西,才能够使他们拥有百分百的信仰。正是那种我们所不能够理解的东西,使我们看到永恒的确定性。我们在李路明的作品中正是感受到那个时代的信仰在普通人的神色中所产生的令人匪夷所思的力量。这种力量穿越历史的迷雾重新来到我们的现实中,我们仍然强烈感受到它不可琢磨的力量,我们不得不反思,是什么使得两个时代如此不同?我们的历史是在什么地方改变了运行的轨道的?激情的煽动是怎么有效推翻了一个人与其自我之间的平衡的?为什么仅仅在二、三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就再也见不到那种曾经洋溢在普通劳动者神色中的光芒了?
对于相当多的知识分子来讲,当然会认为多元文化主义要优于单一文化主义,充满差异性的世界要胜过一致性的世界。然而乌托邦的消失,使得人类丧失了对于未来美好世界的想象。在这种前景中,自由知识分子只能从真理走向怀疑论。对于乌托邦时代的批判,李路明则是保持了相当的谨慎性。因为他可能担心自己对乌托邦的批评将会被历史证明是片面的。正像曼海姆的所担忧的一样:“乌托邦的消失导致了事物的一种停滞状态,人类自身在这种状态中仅仅成为一个物,然而,我们将面临可以想象的最大悖论……经过漫长的、痛苦的,却又英勇的发展阶段后,刚好就在发展的最高阶段,历史停止了,成为了盲目的命运,而且越来越成为了人类自己的造物;随着乌托邦的废除,人类也丧失了建构历史的意志,同时也丧失了理解历史的能力。”(德国 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德文原版)
李路明的作品在这样一个商业气氛甚嚣尘上的时代出现,具有特殊的价值,他与那些价值判断具有某种倾向性的作品不同。这种不同恰好消解了过去一元论时代的道德对立原则。他的作品通过对他青春时代的日常化生活场景的经验性描述,回避任何主观的价值判断,从而使得两个时代的价值准则同时失效,这是李路明作品与其他“后波普”艺术家的不同之处。许多同时代的艺术家企图通过花样繁多的变形、并置、改装来证明对历史性的修辞性想象,然而在这样一种被人们不断地变化、涂改、颠覆的假象所包围的情势下,李路明却不再涂改,不再评判,而是接近新历史主义的原则,讲述他个人的故事,以个人自身的历史来理解历史。如是,艺术家所行走的这条道路,在一片混乱的争辩中让许多的人们忽然失语。正因为他的艺术是自我理解的艺术,这种艺术使得所有注释家企图为他再造的纲领性观念都变得失效,包括我。显然,他的艺术对于两个时代的价值体系都保持了警惕性。
看来,对于历史,我们谁都没有多少的把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