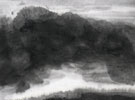【编者按】致力于梳理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艺术评论家高名潞先生再次为中国当代艺术发声,策划大型当代艺术展“意派——世纪思维”,并于六月初在今日美术馆展出。这次展览展出了蔡国强、徐冰、谷文达、黄永砯、张洹等八十余位艺术家的二百余件作品,展示了中国当代艺术这30年来发展中的本土色彩。然而,“意派——世纪思维”展览的推出,却再一次引发了艺术界对“意派”理论的广泛关注和质疑。
“意派”是高名潞先生在2007年总结中国当代抽象艺术时正式提出的一个美学概念,按照其说法和《意派论》一书的阐释,“意派”旨在建设中国当代艺术本土化的理论体系,以本土方式去解读中国当代艺术,从而替代以西方艺术价值审定中国当代艺术的标准。然而,“意派”理论一经提出,便遭受到了艺术界广泛的质疑——是“保守”还是“突破”?是“新”还是“旧”?是具有理想色彩的理论口号还是对现状的实质解读?——围绕这一系列问题,引发了评论界的争论。当争论因为金融危机转移批评视角偃旗息鼓时,2009年“意派——世纪思维”展览的推出却再一次凝聚了艺术圈的焦点,评论也再次烽烟而起。然而,面对质疑,高名潞先生鲜有回应。为此,本刊记者带着疑问采访了高名潞先生,试图能从一个客观、通俗的角度去呈现“意派”之内核云云,与读者共飨。
“意派”:当代审美的文化表述?——对话高名潞
“意派”是一种当代现象
记:您是什么时候开始从事“意派”方面的梳理研究的?又是在什么时候正式提出的?
高:“意派”正式提出是2007年,但这个想法还要往前追溯。其实,我在研究生时,从研究方式的侧重点开始就已经有这个想法了。我不想用艺术就是反映艺术背景的简单的对应关系来讨论艺术史,更希望有一个系统的结构。当我转向当代艺术批评时也是站在这个立场上的,当时对形而上比较感兴趣。艺术表现的是一个内在结构,是一个本质性的把握这和所谓的真实、直观是不一样的。我对极多主义、星星画会等方面的讨论,其实都是和这有关系的。2007年时,当时涉及到表述中国结构和抽象的关系,但是我不愿意用抽象的概念,因为我觉得中国的当代艺术陷入到了一种分割的形式,而这不是出于西方抽象主义的关系。
记:它的理论、架构不是在西方的理论里去架构?
高:对,它是一种上下文出现的背景,是一种当代现象,所以我描绘它的时候运用了意派。但“意派”本身是当代的现象,“意”的概念实际上已经不是古代所指的概念,因为古代的“意”的概念,它还是不能讨论当代艺术。
记:“意派”正式提出时是比较理论化的,也是比较抽象化的,但是“意派”展给许多观众的感觉是说不出来什么具体的东西,您怎么看待这种情况?
高:我觉得这恰恰是展览的目的。这倒不是说故弄玄虚,而是因为它能调动观众的想象力。如果什么事都说得那么清清楚楚,把概念简单地对号入座,反而说明事实本身很乏力。这个展览强调艺术家的视觉创作的一种复杂性,什么是复杂性?复杂性就是一种错位,“看山是山或者看山不是山”,比如何云昌劈柴,你看到柴上写着日期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你身临其境就会知道,何云昌每天劈柴,还是卸掉了一根肋骨,这个就复杂了,他展示的不光是一些木柴,而是展示整个日常行为。
“意派”对应世界关系,是一种方法论
记:在您的“意派”理论和策划的展览中,一直在强调中国特有的文化和美学意义,且不同于西方的抽象,在当代语境下,您认为二者不同的关键是什么?
高:意派不能和抽象对等,从根本上说意派是一种反应世界关系的特殊角度。意派主要就是反对“再现”,因为再现是把外在世界和人的精神直接对应到艺术当中,去追求真实性,我觉得这是简单的、不真实的一种角度。通常,我们看到外界的一个真实情况时,已经加入了自己的意志,所以艺术没有办法把它分离成一种纯粹的真实。
“意派”是对世界关系的一个看法,不是所谓的传统。我只是用“意”这个概念去说明不同的关系,它是一种描述的方法。“意”这个概念是我们古代经常用的,但是“意派”之“意”不是所谓的把传统简单的转化为当代,而是对世界关系一种特殊的解读。
记:观众的审美大都是属于浅层次的,他不会看到特别深,他们看到“意”的第一印象可能就是传统、抽象,这样是否可以从浅层次说“意派”是“中国特色的抽象艺术”?
高:我觉得还是避免这样的对比,最好不要把抽象作为中国当代艺术当中的一个范畴。“抽象”是西方现代主义概念,主要体现在平面的、绘画的,这个展览的类别是很多的。它不但是多媒介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种解释某类型艺术的角度。我觉得可能刚出现的时候,一般人还是以习惯的思维去理解这个概念,有可能拒绝或者排斥它,总是会受到批评,但是慢慢来。
记:从美学角度讲,“意派”是否指向传统美学?您认为它会不会与当代艺术的审美产生冲突?
高:它不是传统的东西,也并不是指向传统美学。比如中国传统里有气韵、神、风、古等很多概念,这个概念总体组成了传统美学,但是“意”其中的一个概念,它本身没有形成传统美学的系统。我们谈“意境”,主要是指诗、画,小说里也有意境,是一种情境交融的东西,它已经受到了西方的影响。 “意境” 首先还是二元的,情境、情景交融;其次它的概括性有问题,还没有办法解释诸多的门类,比如说它怎么解释当代,像耿建翌的《灯光下的两个人》、张洹的《行为欲》、徐冰的《天书》、肖鲁的《打枪》,这些没办法用“意境”解释。但是《意派论》一书中都解释了,而且“意派”展览中的作品多多少少都和“意派”在不同层面上发生了关系,所以这个东西是当代的,怎么能说它是传统的呢?它是当代的生发物,而且也是我个人参与当代,从我个人经验当中生发出来的一种概念。
记:您说“意境”属于二元,那“意派”是不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
高:“意派”不是二元的,它是对应世界的关系的。世界的关系本身不是二元的,是多元的,而且我在书里也提到了海德格尔关于多元性的问题,中国传统很多东西也是多元性的,当代也应该是多元的,“意派”这个艺术理论在描述艺术如何描绘表现这个世界关系的时候,也用了一种多元性的角度。我借用了张彦远的“理”、“识”、“形”三个不同的范畴,你可以把它们看做三个不同的艺术门类、艺术形式或支点去表现这个世界观。西方现代抽象、观念艺术和写实艺术某种程度来说,跟“理”、“识”、“形”是类似的。从手段层面讲,“理”、“识”、“形”就相当于抽象艺术、观念艺术、写实艺术一样,它是工具性的,他们有类似性。但是“理”、“识”、“形”是互相重叠的,交叉的,而抽象、观念和写实是分离的,极端的,这是我的发现。借用它变成当代理论进行描述是没有人做的。
“我希望有人找到我的硬伤”
记:“意派”展览,包括了几十位艺术家在不同时期创作的重要作品,但很少看到现在市场非常红火的艺术家的作品,为什么?
高:其实这里也有市场上表现很好的艺术家的作品,像蔡国强、徐冰、展望等人,可能他们不如架上绘画市场市场表现的红火。但他们从事多媒介的艺术创作,架上、实验等多种形式。
市场表现不是我选择艺术家的标准,我主要是看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本身的特点是不是和意派发生了关系,和意派的某些东西契合,这是我策展的角度。
记:有评论说您有很浓的89’情结,他们说看了这个展览,发现了很多艺术家是曾经参加过89’中国现代艺术大展的,也是您很熟悉的,您怎么看?
高:首先有很多参展艺术家是我不熟悉的,其中年轻人也不少;其次,即便是熟悉的,也是因为他们的艺术创作是有一定延续性的,因为意派当中一个比较重要的特点就是:持续性,就是它有一定得内在逻辑性、延续性和稳定性。假如一个艺术家开始是进行实验性研究,后来又突然去走市场路线去,这肯定不行,这个艺术家的艺术探索必须有自己既定的目标。
因为延续性本身说明一个问题,它排斥了一种功利性,无论怎么变化都是有内在逻辑的,还是相通的。但是如果这种变化只是为了外部的因素去做,那肯定是不符合这个展览的。
记:“意派”是不是不仅适用于艺术评述,也适用于政治、文化、经济等评述?
高:“意派”是对世界关系的一种看法、一种视角。如果我们对于世界关系的看法和表现方式有多种,那么意派就是其中的一种。它不但可以从艺术角度表达对世界的看法,同时还可以从政治学、社会学或者经济学角度进行表达,也可以从政治体制方面进行梳理,应该说,它是一个方法论。
记:这次展览是不是对“意派”的一次实践?当时有没有考虑理论和现实的关系?
高:考虑到了,我觉得应该说理论和实践是互动的。策划展览,要求批评家、理论家有一种概括能力,需要一个理论的基点,就这次展览本身和理论建设的本身来说还是互动的。
记:“意派”和“解读意派”这两个展览结合起来,有没有达到您的期望或者目的?
高:我觉得达到了一部分吧。但是“意派”展览时间太短了,这是我的遗憾。现在也有人评论、批评,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建设性的批评还是破坏性的批判,都是好的,我的态度都是一样。但是现在我觉得还是有点失望,因为我现在看到的批评还不是我所期待的,不管是批评我还是赞扬我,都应该进入一个实质性的问题,我现在感觉批评还是外围的批评、口号性的,这不是我期待的。我希望有人找到我的硬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