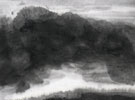当代艺术在经历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精神高蹈、九十年代的语言狂欢,直至近几年艺术市场的喧嚣之后,仍向着奇观式的中国现实景观继续挺进。反思历史、批判现实、反讽经典是艺术家们着力最多的创作倾向。而陈淑霞的艺术却显示出一种别样的审美诉求:她往往通过一个或几个纯情的女孩子的童年视觉,或具体的景物去感触与组织这些如梦如幻的内心向往。她对于日常生活经验的表现和想像是借助于感觉来表达的,或者说她的视觉叙事直接来自于她的感觉,在她视像中似乎有意回避了对复杂,甚至残酷的历史、现实的思考,而是把思考转让给观者或评论者,而让自己专注于情感和感觉,使塑造的形象鲜活而生动,带有童稚般乌托邦式的迷茫与憧憬,很少感受到来自历史和现实层面的直接压力,从而构成了她艺术最鲜明的特点。
她以个人的日常生活经验为想像对象,将艺术渗透在日常生活的场景之中,看上去平铺直叙,像是没有经过剪裁和提炼一样,犹如一泓清水,简约,但也很清澈,给人一种平淡、自然、直率的美感,不含有对现代城市日常生活进行否定的意味。这反而使人感受到她对温情脉脉的日常生活的怀念,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安稳、细腻的人生况味的悉心体会和咀嚼。其实,生活本身是错综复杂的,经过简化和提纯的想象,一定显得单纯、清丽,而且意味深长。她塑造的形象也许模糊了一些而不够逼真的写实,但却让人感到更加真实,更加自然,更具有生活的实感和厚度,也传达出更多的思想内涵。情交流和情绪变化,也在同一个画面中得到了充分的、自然的表现,从而把艺术家对于角色的主观干预隐藏得更加深而不露,并且避免了过多使用特写和近景可能给观众造成的强制性约束。
《野山》在视觉表现上力求还原生活形态的原貌,镜头给我们描述的陕南山区的生活环境和自然景观,那层叠无尽的山峦,大大小小的坡腰和山峦脚下光线幽暗的农家土屋,都保持了山乡风貌的原生美。这是一种真实、质朴、平易的美,也是一种粗犷、朴拙、雄浑的美。影片的主调是冬天,石土混杂的山峦蒙上一层灰黄的色彩,灰灰家的黄色土坯厦房,坐落在画面的突出部位,给人一种凝重、荒凉的感觉。当镜头分别进入灰灰家和秋绒家的时候,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依然是几乎不加修饰的“自然景观”。 但就在镜头给我们展示生活的“自然原生形态”的同时,导演还要求这种展示必须是藏而不露的,不着痕迹的。也就是说,影片既要保留秦川山乡风情画的自然色泽,又必须赋予这种自然的美一种艺术的韵律和意境。电影是光和影的艺术,光和影就是将原生形态的生活雕凿成艺术品的刻刀。不过,《野山》对光和影的使用是非常审慎的,在许多场合,艺术家们竭力保持了山村的自然光线气氛。我们所熟悉的禾禾、灰灰、桂兰喝酒猜宝的那个镜头,就非常巧妙地利用了太阳落山的一瞬间。屋内外真实的黄昏气氛,凝聚了农家生活的情愫。这里可能集中体现了导演的艺术观和美学观。《野山》是以视觉厚度见长的,但它在表现上始终显示了很好的控制能力,把握分寸的能力。所以,《野山》在整体上给人一种诗意的感觉。这种诗意有时并不就在表现了鲜明的倾向性的地方,倒是在那些模糊的、说不太清楚的地方。比如秋绒刨地,灰灰吆牛犁地,卸了套的牛悠闲地吃草,灰灰躺在翻起的土地上,把栓栓举过头顶,这一组镜头所表达的其实正是农民的理想,农民的幸福,农民的乐趣,这种对土地的眷恋,是灰灰和秋绒感情的连接点,农民精神世界中非常美的东西和非常可悲的东西也都凝聚在这一点上。
庄子讲过一个寓言,把这种古典审美精神表述得非常准确,他说:“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这则寓言形象而又含蓄地表达了中国传统美学对于美的一种认知,《野山》在某些方面沟通了这种认知对我们能切实感受到画面整体和谐的艺术效果,以及那种与她内心直接交流的温暖和感动,达到了力避斧凿,纳技巧于心理流程的审美境界。在我看来,和县城之后,她眼界大开,内心逐渐发生了变化。她并不甘心像老辈子人那样,把八寸厚的磨盘磨成四寸,从姑娘熬成了老太婆;而对山外新的世界的向往,使她对禾禾的感情慢慢由同情发展到理解和爱。她最后和禾禾走到一起,并不是她刻意追求的结果,也不表现为一个由此及彼的必然过程,在这里,桂兰只是恰好赶上了一个吹醒她内心欲望的时代,和点燃她心中火焰的人。 影片对二水这样一个小人物的处理也力求建立在生活逻辑的基础上,而并不套用某种现成的固有模式。二水的出场是在秋绒家门前的道场上,一副死皮赖脸相,但他后来在影片中的基本走势却又出人意料。他与禾禾的更多接触,以及他对灰灰的醋意,使这个游手好闲的“二流子”多少也感到了劳动的乐趣,多少也表现出一些“正义感”。于是,我们看到,影片结束时二水已经不是一个单色单质的小丑形象,他的色彩丰富了许多,也浓重了许多,他绝不是一个僵死的“坏人”,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的面貌也许模糊了一些而不够鲜明,但却让人感到更加真实,更加自然,更具有生活的实感和厚度,也传达出更多的思想内涵。其实,生活本身就是错综复杂的,经过简化和提纯的生活,一定显得单薄、苍白,而且乏味。
80年代以来,纪实美学成为一种流行时尚,长镜头理论受到许多电影理论家和艺术家的盛赞和推崇,安德烈?巴赞一时成了中国电影界的“圣人”,有许多人开始用怀疑的目光注视以往电影中司空见惯的戏剧性和戏剧的表现手法,也有人寄希望于电影与戏剧的“离婚”。在这里,“故事”、“情节”都已过时,人们要求看到的是非剪辑化的生活,为此,人们做了各种各样的探索和实验,而《野山》是这些艺术实验中相当成功的一次。这种成功主要不在于长镜头的数量在镜头语言系统中究竟占有多大比例,而在于它们实际上已经超越现有的实验性结果,进入了民族生活和民族心理的表现层次。在这里,更重要的不是讨论镜头的长与短,而是领悟时空延伸当中涵义深与浅的问题。所以有人说,《野山》消化了几年来大家共同探索的成果,把长镜头语汇贴切而有机地化入了中国电影镜语系统之中。
一般说来,完全套用长镜头理论拍摄的影片未必适合中国观众的口味。然而《野山》在镜头运用上大量使用长镜头,却并不使人感到单调、沉闷和压抑,反而收到了与影片整体风格和谐一致的特殊功效,甚至让人感到,这可能是完成这样一种美学风格必不可少的艺术手段。观众之所以对相对静止的镜头始终保持了“注视”的兴致,恐怕就在于镜头内部的“动作”所传达的层层递进的涵义。长镜头的奥秘就在这里。例如禾禾、灰灰、桂兰猜宝那场戏,影片用了一个三分多钟的长镜头来表现,前景是禾禾与灰灰一左一右坐在小饭桌前喝酒,后景是桂兰在门外筛玉米,暮色苍茫中,不时有三两个晚归的农民从洼中小道走过,和桂兰寒暄几句,远远地传来歌声和牛叫声。在这种真实的生活气氛中,镜头静静地停在那里,摄影机尽量不动,必要时徐徐而动,客观而平静的镜头细细地展示出三个人物各自的心态。演员的状态也很好,松弛、自然、逼真,味道也很浓,我们能切实感受到那种与他们内心直接交流的温暖和感动。还有禾禾养柞蚕失败,“夜会秋绒”(215英尺)、桂兰被迫离婚后与禾禾“夜饮庵房”(230英尺),以及我们前面提到的影片结尾灰灰和秋绒磨面那场戏(131英尺),在这些镜头内部,导演分别运用缓慢拉摇、全景缓慢推成中景的拍法,静中有动,虽动犹静,创造了整体和谐的艺术效果,达到了力避斧凿,纳技巧于心理流程的审美境界,准确地呈现了此时此地人物的复杂心态。它所包容的丰富内涵是其他镜头语言所不能比拟的。
长镜头理论是巴赞电影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德鲁斯在归纳巴赞学说的“中心论点”时曾经这样说过:“艺术家的视象应当是他选择现实而不是改变现实的结果。”这种选择所以同样能产生艺术,是因为摄影机能挖掘出“经验的现实的对应和相互关系”。在巴赞看来,“银幕上的画面一般不应代表另一个全新的想象的世界,而应代表作为其本原的那个世界。艺术家首先必须是一个卓越的观察者:他应该从一个事件的整体或者一个特定的世界中,挑选出那些能完全表现出这个整体或者这个世界的那些部分。”事实上,当上面提到的那些镜头画面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感受不到这种选择的魅力。这种不动声色的选择,恰恰包含了导演对于现实生活形态的整体性把握。
不过,《野山》在镜头运用上并不为长而长,导演对镜头语言的选择,事实上更多地考虑到了所要表现的内容和影片的整体风格,以及对现实主义的美学追求。在这里,长镜头语言所发挥的“视觉还原”功能,最大限度地保存了生活的完整性和现场感,保存了生活的原貌,人物间细艺术家首先是一个卓越的观察者:他们从一个事件的整体或者一个特定的环境中,挑选出那些能表现出整体或世界的那些部分。当陈淑霞的这些作品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感受不到这种选择的魅力。这种超验的选择,恰恰包含了陈淑霞对于现实生活形态的整体性把握;恰恰是在这种与世隔离的视域里,把情感中的利益剥离的干干净净,人物形象才显示出稚拙、纯朴。在将所有装饰性的阐释都剔除之后,生命呈现出了它的质感和可以触摸的感觉,这是生命之美。
尽管她不是简单直接地表现现实的复杂,但不过这也许反而成就了她的创作。因为远离现实使她的艺术保留了她寓情的细末微节,凸现了作品本身的质感与神秘。我们在观看她的作品时常常会遭遇到这样的细末微节。她是从现实的个人经历中提纯美好的片断,去排遣、释怀她的记忆、爱好,重新寻拾梦一般的自由与憧憬,营造她在喧嚣的混世里无所谓的自我表现与独领风骚。呼应和营造了这种相隔、间离与隔望的效果。从这一点来说,她又是非常真实的,她真实地表现臆想状态下的内心世界,可谓是一种在内心折射的抽象现实。作为对现实浮躁的“代偿”,陈淑霞的审美趣味得到了寻常的发展,并形成了相应的唯美唯艺的视觉样式。这体现在她人物的意像而成为陈淑霞自身意趣的缩影。她毫不避讳地表现出自己对臆想中的超现实生活场景的感性认知,甚至对她自己油画语言风格的迷恋替代了作品所画形象的兴趣,使画中的“她们\它们”无言地透出一种近于闲适、慵倦、靡丽,甚至有些颓废的心态。这似乎是中国传统文人伤感主题在当代文化土壤中的延伸与演绎。尽管当今早已失却了恬静的桃花源式的存在土壤,不必也不应该去比附新旧文人的生活方式和态度,但作为文人自创和承传的题材,她画中最终指向是通过封闭的“相隔有多远”来达到自由的境界,似乎可以看出她接续着前代文人对女性和女性对自身的审美取向。
长久以来,不仅个人化的唯美丽辞一直被那些追求宏大命题的艺术家所轻视,而且,它所表达的价值和渴求,以及它营造意义的可能性也不断地受到质询和怀疑。但这恰恰从另一方面给予个人的视觉艺术表达一种存在的理由,说明它应该在视觉艺术表现和想像中占有一席之地。或许,正是由于宏大的历史与现实的质疑与批判常常陷入一种空洞的尴尬,才赋予艺术家的主观意绪投射到那种诗意的幻想性语境中,在借助人物的成长感受和理想来传达灵性的叙事话语的必要价值。陈淑霞这种对生活中美好的憧憬、检视及体察,才使得现代城市生存所带给我们的焦虑,以及由此产生的苦闷和枯寂的心境或被消解,并成为一个值得思考的意义范畴和思辨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