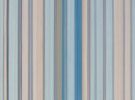“凡是可说的都可以说清楚,对于不可说的一定要保持沉默。”
“确实存在着不可表述的东西。这种东西显示自身;它就是神秘的东西。”
“神秘的东西并不是世界怎样存在,而是世界存在。
——维特根斯坦
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逻辑中,不可说的东西正是我们生活中最有价值的东西。美学就是这样一个超验的领域,它只能被显示,不能用语言加以表述,而抽象艺术更是其纯粹化的表征。
当前,中国人对于抽象艺术往往有着约定俗成的认识。从宏观层面上来看,它泛指那些从写实主义出走的,更多地追求形态语言、色彩、造型等方面自在的表现能力与审美价值的架上绘画形态。这当然称不上一个严谨的定义,但是它却比任何定义更接近于大众观念中的“抽象”形象,因此,这一认识比微观意义上的“抽象艺术”概念得到了更多的认同。
这一认识,为抽象艺术赢得了更广泛的受众,却也影响了大众对于抽象艺术的理解深度,并在一定程度上反过来影响着抽象本身更深地扎根于本土艺术之中,构成了当前中国抽象艺术家所必须面临的现实悖论。一方面,宽泛的定义与易于识别的视觉特征使得抽象艺术的创作更易于成立;另一方面,更多停留在视觉识别与联想比附层面的认知与阐释方式,也使得抽象在当代艺术格局中由于话语对接的困难而逐渐被边缘化。于是,抽象艺术家难免曲高和寡,而抽象欣赏者则往往不知所云。
因此,当我们解读中国抽象艺术时,不得不依赖于由视觉经验与主旨阐释所构成的关于艺术家的知识背景的了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过程更接近于一次解码,解读画面背后的情感世界与思路历程,只不过它并不会依赖于图像学式的符号分析、对主题性与叙事性的追认与体味,而是依靠于笔触、色彩、线条、明暗、对比关系等绘画语言本身的修养与感受,进而品味与把握艺术家的创作主旨。可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回归到了经典的审美逻辑中去了。
就个体抽象艺术家的作品而言,我们不能从一种整体性的方法论体系入手,而只能从视觉语言的形式特征出发,归纳出艺术家自身的表达思路与话语逻辑,从而获得某些具有本土意义的方法论特征来。此次李磊与古原的作品展,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契机。
李磊与古原的抽象作品,都脱胎于表现主义的源流,得益于自然景观与人文气韵的涵养。这在走向中国本土化的抽象艺术家中,具有普遍性。如果说,在西方,抽象艺术的诞生是出自西方绘画体系自身形态语言的发展轨迹与艺术、思维逻辑演进的必然结果,有着明显的线性轨迹与单向性的上下文关联的话,那么,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艺术实验进程中,作为一种形式语言而引入的抽象画,最初是从完整的理论体系中抽取出来,充当一种突破写实传统的观念禁锢、彰显创作自由的前卫性工具而存在的。因此,它便与自由思潮中的表现主义传统有着天生的关联,而与中国传统中的写意脉络遥相呼应。中国的抽象艺术,在诞生之初,更多地继承了热抽象的发展脉络。它更感性、更富有情感、更多地自觉依附于中国传统理论与既有的西方哲学体系,来抵消话语缺失的单薄感。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艺术家便显示出各自独特的艺术品位与价值取向。
李磊的抽象艺术作品,肇始于1997年开始创作的《禅花》系列。《禅花》的创作,在更早期的《太阳鸟》、《月亮蛇》等一批带有浓郁的表现主义倾向与象征意味的作品中寻得渊源,进一步通过装饰、平涂的表现手法将画面空间与表现素材转向平面化与抽象化。正如前文所述,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转变过程。但是经历了这个历程之后,李磊的创作便很快地迈向对形而上的思辨系统的追溯与展现。同时,这种追求也与艺术家自身的知识体系中的传统学识、宗教信仰与价值追求相结合,成为艺术家实现自身精神追求的一种主要途径。
当然,艺术家不再仅仅将作品视为一种自我修养、反躬自省的途径,而将其付诸公共领域,去寻求一种沟通与认同的时候,它便面临个人编码的转译过程。正是这种对接的困境,催生了他以《海上花》系列为代表的一批成熟作品。
李磊曾经将自己的抽象艺术道路归纳为四个层次的问题,其中涉及创作领域的主要有三个,即所谓的视觉音乐实践、诗化自然意境与生命直观体验。这三个主题之间在时间上略有穿插,并不是完全的取代关系。《海上花》系列,在这个体系中起到了承上启下、沟通连接的作用。它上承艺术家对于“禅”、“道”统摄下的形而上的追问,下启一种化朴素为绚丽、变单纯为丰富的风格历程。这也预示着艺术家的创作心态由自足的内省向开放的对话的转变。从《禅花》到《道》,艺术家完成了自己“生命直观体验”的形成过程,而从《海上花》开始,艺术家试图将这种体验映射到周遭的对象与物事之上,以期将这种体验化为一种可以共鸣的通感。由此,“诗化自然意境”与“视觉音乐实践”的谱系得以开创,这些作品,既是在创作深化的基础上进行的主题差异化,是对于“生命体验”的对象化,同时也是在话语系统上的具体化。他们共同构成了李磊构建的对于自己的艺术体验的立体化阐述。
《海上花》系列,奠定了李磊抽象艺术形态转变的基础,也开启了其将抽象艺术思维与感官体验外化为一种通感体验与生活哲学的开始。它体现的是一条本土的抽象艺术由形而上的精神性抽绎走向主体经验外放的精神性的、更“本格”化的艺术道路。
古原的艺术创作,则更多地践行了一种情感风景与人文意象的抽象化道路。古原曾经长期从事西藏题材的绘画创作,但是不同于多数艺术家着力于对于异域情调与民族风情的展示,古原的作品,更多地将西藏作为自己对话与观想的对象,是一种“有我之境”的展现,这也许与艺术家早年的国画创作经历有关。因而,古原早年的西藏题材,很快地走出一条中西艺术感觉融合、中国意味与表现主义相结合的油画本土化的个性道路。对于对象与景观的情感化展现与抽绎,很自然地导向了对抽象领域的进军,这与艺术家对民族题材的“得其神而忘其形”互为表里。而直接生发于表现主义人文景观的古原抽象画,在作品中还是潜藏了一些风景画的基因,那便是在色彩运用与线条挥洒上,不仅仅是运用观念色,以及运用线条自身的表现力,而且还显示出强烈的、西藏特有的、绚烂多彩的光源色与闪烁的变幻效果。在其以日期命名的这一系列作品,以及吉祥天书系列中表现得更明显。无论是映射着经幡、庙廊抑或其他意向的作品,都笼罩在一片强烈、闪耀、充满动感的光影色彩之中。古原的西藏系列作品,并未完全走向磨灭形体的纯抽象领域,而是将一些具备对象形态特征的图像与造型融汇在整个色彩构图之中,展现出更强烈的动感与节奏感。这显然与长风猎猎,骄阳高照的西藏景观有相应之处,也预示着古原的这一经典系列在精神依托上并未转向形而上的思维与形式相对应的抽绎道路,而是转向了以传统的感悟山水的“有我之境”式的抽象体验道路。
与此同时,古原还尝试了一批以人体、带有具体物象形态的观念性更强的作品。观这些作品,色彩语言更偏向主观性,表现手法也更趋于主题性、观念性,除了在技法语言上的抽象形态以外,与其他具象绘画之间表现出互通性,这也显示出古原在创作上更愿意去接受任何一种不同的创作倾向。正是这样的意义,古原的创作,把中国抽象在引入阶段就强调的工具属性体现得尤为充分。
由李磊与古原作品所组成的展览,体现了抽象艺术的多面性。两人都立足于对生命的意味与体验,然而,一者更侧重于对艺术体验精神化的抽绎,精神体验的通感与转化,另一者则侧重于对于生命体验的对象化与对象的虚置化,通过对对象的抽绎而留存感觉的传达,摆脱具体情境的束缚。一者由内而外,是形而上的精神体验向形而下的生活哲学的外化,是一种自我体验的诗意化的阐释与表达;一者则由外而内,是感物萦怀的传统向更自由的表现手段与形态语言的解放与提炼,继续了一条由表现主义向抽象艺术进发的道路。他们的并置呈现了中国当代的抽象艺术两大主要的发展趋势,体现出中国抽象艺术的发展状态与基本特质,而且在本质上是向一种精英主义式的阐释话语与观看方式的回归。这种回归对于观念盛行、符号泛滥、图像的趣味大行其道的当下,有着不同以往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