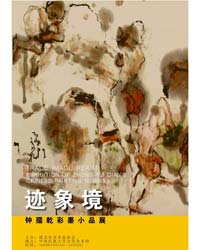那隐隐的边界在消褪
而狂欢 恰刚刚开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化界的开放使得大家仿佛进入了一场自我想像式的世界主义狂欢。具体到艺术领域,中国艺术家们从开始的小心试探到大力拥抱西方,试图用短短十年的时间奔完西方艺术从现代主义萌芽到后现代艺术的百年历程。继而,在后文化时代,中国当代艺术的图像大餐亦粉墨登场。
而此时,西方艺术史家与哲学家们慎重地抛出:艺术走向了终结?正是在中国美术界轰轰烈烈闹八五新潮的前一年,美国艺术史家阿瑟·丹托经过反复的逻辑推理与论证,认为艺术已经走向了终结。在丹托看来,至少有三个原因让他提出了终结论,其一是哲学对艺术的剥夺;其二是艺术自身的身份危机;其三是当代艺术尤其是美国艺术的多元实践导致了对艺术史内在结构、逻辑或秩序的消解。
二十多年后,各种艺术类型——尤其是架上绘画仍然繁荣,曾经被质疑的装置或影像等形式早已为人们所笑纳,终结论却也反复被理论家提起。我们慢慢对各种终结论——无论是历史的还是文本的——出现了审美疲劳乃至置若罔闻。而当代艺术界的现实可谓是对丹托三个问题的反证:如今哲学理念先行的观念艺术大行其道;现成品构建的艺术不再被人们质疑;美学退出了艺术理论的视野,有序的结构连同德里达的解构一起被扔进了后历史的垃圾箱。艺术没有终结,终结的只有被设定的边界。艺术,进入了一个无边界的时代。
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追问:这与虚构或真实有什么关联?终结论在某种程度上是线性艺术史的逻辑推演,而一部艺术史却实在是虚构与真实辩证关系演变的历史。贡布里希的笔下只有艺术家,艺术家个体的创造从来都离不开虚构的艺术手段与方式,而宗教的精神性真实、视觉的高度仿真或者哲学意义上的形而上真实是特定时期不同艺术家们的最高理想。当二十世纪的摄影、影像与数码技术越来越嚣张地直接呈现出“真实”可感的视觉世界,甚至物品直接进入艺术作品领域,传统绘画由“虚构”而“真实”的单一路径的合法性似乎成了一个悬置的问题。
如今这个数字化生存的年代,我们被二进制计算频繁地升级换代。我们不仅来不及厘清艺术的边界,甚至很难分清楚:是我们创造了虚构的世界?抑或是我们原本来自虚构的世界?网络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存方式,这个虚拟的空间,既不同于现实的物质空间,也不同于传统哲学家与艺术家大显身手的精神空间。某种意义上它类似于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的眼中的“第三种空间”。在这里,主体性与客体性、抽象与具象、可知与不可知、虚构与真实混杂在一起。这个开放的空间既容纳了我们无限的想像,也让我们认识到真实的有限性。在这个空间大挪移的时代,源自真实生活的影像被数字技术反复虚构,成为“陌生化”的幻觉;被人为虚构出来的架上作品,却又在真实的内在触觉中反复咀嚼着艺术创造的意义感。
具体而言,本次展览将架上绘画与影像作品并置,共同呈现一群青年艺术家对虚构与真实问题的当下思考。套用时下的潮流,用代际来指称这群艺术家,可称作泛七零后。六零后、七零后、八零后或九零后的划分,也许只是个简便偷懒的分类法。个中道理确有一二,可视作中国社会变迁的符号学划分。比如,六零后恰好是文革后接受中国大学精英教育的一代,既赶上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化思潮也赶上了九十年代兴起的市场大潮;八零后是独生子女第一代,他们从出生伊始就被打上美好新时代烙印。刚好,泛七零一代即六零末期到八零初期出生的这代人,在九十年代接受教育,赶上了市场经济大潮又存留着一丝文化理想主义情结。这样一群“夹心层”,正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升级版本。
他们有节制不张扬,更重视个体的内在体验。宏大主题与使命感不再以集体的方式呈现,个体对对外界的敏感、对存在的领悟与个性化的表现方式才是要点。他们低调有修养,这修养要感谢上一代艺术家即他们的老师辈。经过八十年代洗礼的前辈们授之以中西文化的精华,他们自己又享受着地球村的种种便利。对艺术和对自身都充满了自信的他们,不屑于急躁地将媚眼抛向任何他方。他们久在边缘,而边缘刚好具有无限的生发性:现代性与后现代的分野不再是问题,去中心化与去西方化也来得自然而然。勇于打破任何设定的边界并且文化身份意识淡化的这一代,真正具有世界主义的宏观视野。
但是,在日益被虚构的城市空间、在日渐沉沦的虚拟生存中,泛七零一代的去集体主义某种意义上也直接展示着当代人的疏离与孤独。没错,在这个只信奉部分真理的时代,孤独,才是存在的最真实意味。
朱清华
2011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