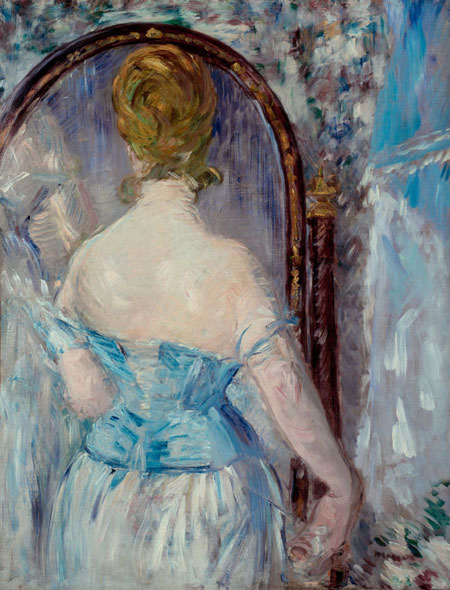披头士乐队
在一件艺术品面前,我们能看到什么,或应该看到什么?我们很容易辨识电视上关于美军虐囚的图像,但在一幅波洛克的作品面前,这个问题就凸现出来。上世纪七十年代尚流行一种二元的观看模式,也即人们在接受艺术作品时,分别从视觉(visual)和符号(symbol)两个层面来解读意义。前者反映了自然如何原原本本地通过色彩、线条、构型再现在作品上,被划为看(see)的行为;后者则反映了对惯例和习俗的读解,类似于口头文化中的阅读(read)。但这种泾渭分明的区分却易于陷入窠臼。如,19世纪由于科学的发展,艺术提倡用无遮的眼睛(innocence eye)去观看(拉斯金语)。但无论是康斯太勃尔的水彩风景,还是印象派的描绘,不管他们如何辩解自己与传统背离,我们都无法在他们对前人技法的因袭及自己无遮之眼的辩解中,清晰地区分作品究竟是视觉的,还是符号的。
那么,我们如何观看呢?潘诺夫斯基曾举例,对达•芬奇《最后的晚餐》,基督教世界的子民很容易了解其题材的宗教含义,而处于蛮荒之地的生番至多知道这是一次集体聚餐。他的理论暗含了一个前提,即对于意义的理解差异,是建立在彼此隔绝的文明之上的。在信息网络覆盖全球、比特速率高速传递的时代,潘氏的图像学理论就显得不那么熠熠生辉了。
今天,无论是西班牙人、俄罗斯人,还是美国人、中国人,在面对麦当劳、迈克尔•杰克逊、毛泽东的图像时,都能得到一种约定俗成的意义,不管这种约定俗成存在多么细微的差别。图像时代告诉我们:只有想不到的,没有看不到的。它恰似又一次播撒大地的福音,只是图像的无限繁衍,带来的是意义的贬值。这是一个平面化的时代。图像学所处理的,已经由一种人文价值下降至一种观看的视角。在不恰当的地方运用,只会出洋相。如披头士乐队1969年著名唱片《修道院大街》(Abbey Road)封面,四名乐队成员排成单行,步伐一致,穿过马路。细致观看,会发现第三名成员保罗•麦卡特尼是光脚行走。光脚走路是西西里人古老的丧葬标识,那么这幅画从图像学解读,是说明保罗正行走在为他送葬的圣地上吗?从理查德•豪厄尔斯那里,我们知道那仅是由于在唱片封面的持续拍摄中,保罗觉得难受便脱掉了鞋。在当下语境中,用图像学的方式来寻找隐秘和晦涩的符号世界,反而成为了一种极富喜感的反讽,如同纳博科夫的小说引人发笑。
以上所说的两种方法,刚好从两个方面说明了解读图像时,单一价值准则的失效。前者是注重形式的,后者是注重内容的。它们相似的共同点,就在于寻求艺术作品的本原意义,并坚信它存在着。尽管随着今天理论的多元化发展,各门学科的融入不断拓展了人们观看的模式,但本原意义的幽灵却无时不在地游荡着。
比如,观看毕加索的《格尔尼卡》,我们借助精神分析的方式,来阐释这部伟大的作品如何向观者传递作者的情感,以及观者如何捕捉这种情感。借助于一些零碎的资料,我们又走上了图像学的老路,但这一条道路是通往世俗的。我们获悉公牛和马在毕加索的作品中占有显著的地位,并在图像与毕加索的童年经验之间建立起绝妙的联系。从而在对图像私人化的根源探索中,保留了作品的崇高品性。但正如贡布里希所言,精神分析所建立的图像阐释方法正如钢丝上行走的戏子,命牵一线。
再如,约翰•伯格发人深省的意识形态方法。他关于小汉斯•荷尔拜因《大使》的评论引起广泛争议。在他看来,大使身上奢华的毛皮大氅,墙上华丽的帷幔和桌上的地球仪,无不反映了艺术赞助人身为新兴资产阶级,对于财富、权力和名望的占有欲。但他忽视了在画的前中央,有一个变形的头盖骨——死亡的象征。由于它的存在,使得绘画完全可以从截然相反的立场解读。
在图像时代说图像,它不仅体现为一种绝对的、人文主义立场的价值准则失效,也体现为作为主体的作者和权威阐释者的死亡。而后者又恰好对应了那种非此即彼的二元模式的终结,并应和了一种讲求差异、却无他者的时代已经到来。福柯在《词与物》中,提供了一种难以理解但又精彩绝伦的反讽,来说明再现模式的荒谬,从而印证了主体时代的终结。他说,如果古典世界仅由再现组成,那么它就不可能同时包含一个留给站在艺术作品之前的观者的位置。对应于今天,则是当不同种族的人共同观看《最后的晚餐》或者007系列时(无论是印刷品,还是拷贝),当我们用不同的语言说同样的思想时,我们应该看些什么?这正契合了戴望舒的那首诗: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