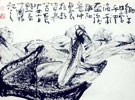巴赞的现实主义观
罗森告诉我们,阅读巴赞对现实和电影的评论,人们必须一方面记住所指——“客观真实”,另一方面要记住“人类主观处理对象的过程,这些本身构成了巴赞立场的基础”。
也就是说,尽管可能不干预物理现实,但通过摄影机镜头看到的世界告诉我们的东西仍然比电影摄制者努力表现的现实更具有主观性。罗森对巴赞立场的看法是:
“客观 总是受 主观 影响,不经过后者的加工,便是无法得到前者。”
所以,人们无可避免地进入一个 现象学 框架。正是从这个以及其他美学角度,巴赞用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式看待整个电影的历史和演变。用他自己的话说,存在“相信影像的导演和相信现实的导演”。
巴赞关于区分“这两个宽泛且对立的趋势”的立场包含的不是一种电影风格与另一种的相对,而是两个相反的塑造现实的观点,两者都是完全主观的。
应该明确指出,电影的历史并非只是关于风格的讨论。若我们将德国变现主义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相比较,很明显,我们面对的不仅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而是对现实生活两种不同的艺术变现形式。
于是,这两个“相反趋势”的差异来源于同一种认识,即离开叙事的语境意义,便无法理解和阐述电影的画面和声音,这产生于导演自己的思维框架。该思维框架在于导演从其自己“先在于”立场看待感兴趣的目标时所采取的形式方法。因此,正如巴赞所见,关于现实在电影中的标准位置,这个伟大的划分基本上处于两个主张之间。
即一方声称现实先于、且完全独立于艺术知识,而另一方相反,声称艺术知识定义现实(现实依赖人们的理解的不同而不同)。
两个叙事框架
尽管这两个方式之间存在根本的差异,但鉴别两者都是对于现实的主管表述,所以任何一方都不能声称比另一方更加真实。实际上电影影像无非是对现实的一种自我的、人性化的描述,并依据所采取的方法,变成两种现实观,从两种相反的主观立场中折射出来。
从电影叙事(故事)观点来看,这两种先在的立场(主观性)将巴赞的划分置于更加细致的研究之下。
有在叙事图谱的一端开发“客观叙事”的导演,也有在另一端开发“主观叙事”的导演。
前者,如格里菲斯、普多夫金以及爱森斯坦。他们将自己的叙事分成“好”和“坏”两个截然对立的阵营,分别以“好人”和“坏人”为代表。而在后者中,如德国表现主义电影,叙事中这种“好”与“坏”并非分开的。而是集中在一个个体的内部中,个体的他或她在自己内心体验着这些矛盾。
所以,在客观叙述背景前提下,叙事往往是外向的,向外注视着这个实在的、可观察的感官世界,聚焦于相互对抗的身体动作。反之,在主观叙述背景下,叙事在心理和生理上都变成内向的,冲突高度符号化的。
由于是对立的,双方都可以出于各自的立场去否定对方。如茂瑙拍摄于1924年的《最卑鄙的人》中的主观性令格里菲斯1919的《凋谢的花朵》的现实主义显得“不真实”,而格里菲斯的客观性让茂瑙的心理手法像“虚构”。在茂瑙的《最卑鄙的人》中一切始于完全可信的、理性的事物,不存在理性无法把握的东西。反之,在格里菲斯这边,一切始于实际生活中能观察到的,以及人们可以凭借感官体验到的东西。
因此,对主观叙述而言,“现实”是精神上的(理性的)和不可捉摸的;对客观叙述而言,“现实”是感官的。整个情节是“有与无”情景中的一个悖论。也就是说,如果人们强调茂瑙的《最卑鄙的人》中呈现的内省或虚幻的思维定式,就会错过格里菲斯的外向思维定式,反之亦然。但悖谬的是,不包含对方,两者都无法追求其自身的内向或外向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