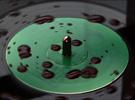在陈皖山看来,艺术创新被看成是比艺术本身还要重要的一个原则。他总是醉心于各种不同的艺术题材、风格和技法的探索,游走于不同的媒介物之间,几种不同的艺术风格并存,这其中主要目的就是反对人为的制造以适应市场需求的艺术标签。比如画虾的一辈子画虾,画虎的一辈子画虎,画傻笑的光头就一辈子画傻笑的光头。由于市场营运所产生出的对艺术家特定风格的“标准”或“严格要求”其实等于窒息了艺术家的创造力,是一种对艺术创造本身的终极否定,也是对艺术家人格的否定。
海外的侨居生涯让艺术家重新认识到艺术之根的重要性,艺术家从盲目崇拜西方的文化艺术思想到对其进行有限的否定批判,历经二十载,完成的是又一次的超越。他重新认识到,艺术不仅仅具有世界语言的人类共性,也携带着民族性和阶级性;在政治正确的幌子下,也包含着对艺术话语权的垄断和对艺术作品的解释权。让艺术家深感悲哀的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很多艺术家在不明事理的情况下,在少数国外文化思想和资金的影响下,正在描绘着一幅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包括海外华人都不愿意接受的“肖像”,这类“肖像”不仅违背了中国人民的意愿,同时也违反了以西方人为标准的“政治正确”基本原则,充满了文化价值观的歧视。
使用有色眼镜观察只能产生文化偏差和文化近视,陈皖山对这种偏差不予认同,作品《在信仰的教堂》(200cm x 300cm)就是他的回答。艺术家对近代中国思想界的发展追根溯源,形象地表现出西方各种思想观念对中国的入侵,从基督教到马克思主义都是发源于西方的思想形态,在中国的土壤里都发展出各自的中国特色。它们的源泉关系和社会形态造就了今日的不同的思想意识。观众可以看到这幅作品来源于卢浮宫收藏的16世纪法国佚名画家的作品《美丽的加百丽与玛丽夏·巴拉尼》,这幅枫丹白露画派的作品画的是法王亨利四世的情妇。但是陈皖山通过“借用”与“改造”,无论是思想还是艺术形式都有了全新的意义,艺术原创性在这里更明显地被烘托出来。他画的《万圣节之夜》(200cm x 300cm)是典型的每年十月三十日美国住宅区一景,中国制造的充气卡通人物、动物和神话交织在一起,造成一种时空错乱的画面。这幅作品是根据艺术家的邻居的前院摆设绘制而成的,艺术家有意识地加入神话情节、独角兽和裸体小女孩,并彻底地改变了实际的天空和风景的合理色彩配置,使得这一普通美国民宅景象化生于安徒生笔下的童话一景,让这一孩童节日更具人性色彩。人们从这些画作中清楚地看出,画家对于那种生存环境及其文化理念的领会与理解具有了一定的深度,甚至在他回到了中国本土进行创作时,依然好像还是从大洋彼岸的文化视角或审美眼光来审视,让这些作品带有一点外国味。他对一些中国题材的描绘是用西方神话传说或者文化风俗来阐释和寓意的。这种“时间差”是否也反映了他自己所说的“迷茫”呢?他的《失落》(180cm x 200cm)几乎是一张自画像,画中人物的自我就像画中人物本身一样,泥塑的形体在水的侵袭下流淌、坍塌,这是艺术家在美国生活的一种写照,也就是当时所处的一种“迷茫”状态。
然而有着学院式教育背景的陈皖山,他始终锲而不舍的是对艺术本体的执著追求,表现出来的就是对于绘画形式技法的研究与探索,对于单纯、抽象的线条与色彩的热爱与痴迷。抽象画《冬日的海景》(150cm x 240cm)和《抽象的光线》(200cm x 300cm)反映的就艺术家在此方面的一种尝试。无创新的几何冷抽象或自由挥洒的抽象表现都已像昨日黄花,几乎没有进一步创新的可能性,因此有“绘画死亡”一说;然而在这里,陈皖山挑战极限,将抽象技法和人的具体印象搓揉。在抽象的条块色彩间组织、运用暗示手法,让观众和自己的经历体验相结合,互动产生出一幅具体而生动的冬日海景图画和一幅明媚阳光穿过玻璃幕墙的图画。
像所有特立独行的艺术家或思想者一样,性格内向的陈皖山经常进行着自问自答的智力锻炼或精神游戏,最多思考的题目之一就是“为什么要‘绘画’”?
自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就有人宣称“绘画已死”,指的是现代派的绘画或者抽象画已死。文化时空行进到“后现代”阶段,艺术红星漫天飞舞,艺术家从走红到消失以陨石般的速度划过天际,他们的原创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金融界的寡头垄断导致自由竞争的消失,艺术家彻底地丧失了作为艺术家的人格与思想能力,沉沦为金融文化乃至一些意识形态团体的宣传项目执行人,成为具体的艺术制作人。装置艺术,地景艺术、观念艺术和表演艺术大行其道。由博物馆或画廊牵线,基金会出资,策展人命题,由艺术家设立的艺术车间制作,成为一时流行的模式。艺术作品不再是放在博物馆里供人欣赏的架上绘画与雕塑,而是一种预先策划好(在固定时间里)的社会行为,可以发生在任何地点,可以出现在任何传媒上。艺术的评价标准直接取决于制作的投资额而不在于其思想性。大型博物馆动则以数百万美元的投资策划一个展览;摄影师花费一百五十万美元的代价仅仅是为拍摄一组人为导演的摄影照片。由画廊经营的艺术家也以十万美元计的费用来制作一些流行项目;而绝大多数艺术家也会认为绘画是一件苦差事,少有耐心和毅力而转向他顾。
陈皖山从来就是一个异类。在经历了十八年之久的海外朝圣与学习,痛苦与徘徊,他认识到西方的艺术模式不可能产生具有真正原创性的艺术作品。和许多美国艺术家一样,寻找一个可以让其没有顾虑的,实现自己艺术想法的地方,创作自己想要创作的作品。很多人去了柏林,他却回到了故乡。在北京,良好的艺术氛围,巨大的工作室,有效的艺术材料供给,还有活跃的艺术思潮,都给了他极大的激励,闭门谢客两年,专职画画。艺术家认为,几百元人民币的投资也可以媲美百万美元的制作,其关键在于艺术家的原创能力和对艺术的认识深度。
2009年10月,陈皖山在今日美术馆举办了回国后的第一次画展。出席开幕式的有艺术家、美术评论家、文化官员及美术爱好者。画家给自己的这次画展取名为“不和时宜”,展出的二十几幅作品像幻灯一样不仅显示出艺术家自身的心路历程,许多作品也折射出生活在那些难忘年代的人们的共同记忆和情感体验。作品提出了一些问题,但答案并非像画面描绘的那样清晰与浅显。很显然,这个“不和时宜”并非“不合潮流”或者“过时”,而是“批判”的一种委婉表述,它是在拒绝当代艺术中流行的(或者说是僵化了的)一些热门题材,是在拒绝火爆市场上的艺术机会主义的引诱,为的是艺术家自己(当然还希望广大观众)清醒地并彻底地从当代艺术教条中解放出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让艺术永具创造性和生命力。
陈皖山在此次画展的图录中这样写道:“视觉游戏是我钟情于艺术的原因之一,我总是对马塞尔·杜尚先生不屑于眼球游戏的故作姿态不以为然。我让自己彻底地从当代艺术教条中解放出来,和那些时尚艺术家拉开距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点、线、面、画画。我无法阻止我自己,就像电影《红菱艳》里的蓓姬那样,一个注定艰难的人生。”
“我让自己彻底地从当代艺术教条中解放出来”。这就是陈皖山深切意识到的艺术宗旨,也就是他重新走向成功之路所认定的方向。“为什么要绘画”是一个至上的命题,也是一个永恒的命题,像是莎翁笔下汉姆莱特的“To Be or Not to Be”一样,这种追问没有终极答案,因此需要永远去追寻与探索。这就是所说的艺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