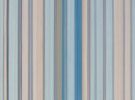众所周知,霍普经常去电影院,有段时间他还为一家电影制作公司当过绘图师。但是霍普从电影中受益的方式非常不同:我怀疑,在《心理》(Psycho)之前,从没有人像今天这样带着惊悚战栗的心情去看他画的那些毫无恶意的、阳光照射的乡村小屋。我的感觉是,一旦涉及到美国式灵魂的流泄,人们就会想到霍普的作品。有意思的是,刚才你提到的两个导演都是欧洲人,他们对美国的想象一定和美国人自己的想象非常不同。
杰拉德·马特:我们继续说欧洲。就像我之前提到的,评论家谈及你的作品时总会提到浪漫主义,尤其是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这可以理解,因为你画出来的情境在某个时刻是可以与之相比的,比如人物总是背向观众,向远方广阔的风景或海洋(作品《海岸》,Coast, 2004)望去,有时候人物的目光也会穿过窗户,投向一片城市景象。在弗里德里希的作品中,这些景象可以说是超自然的;观看者显得很矮小,似乎认识到并惊奇于造物的强大。而你画的风景却没有这么壮丽,或者像你自己所说的:“我对风景中的神性不感兴趣。”那么你使用这些浪漫主义式的主题用意何在?这些画是所谓的“迷宫图”吗?我还在想那些没有人物的画,比如《拖车》(Trailer, 2005),简洁地画了一个蓝白色的工地拖车,自成一体的样子,从巨大的灰色房间的一隅缺口中向光亮中“望”去。我不由想到了委拉斯凯兹的《伴娘》(Las Meniñas):半开的房门,房里家具摆放的次序,镜中的王室夫妇,就像你在拖车上画的那个小窗子一样!之所以提到这些随便想到的东西,是因为我发现在你画作的空间构造中有某种让人不适的、蓄意制造出的错误细节。
蒂姆·艾特尔:我的画当然不是那种“迷宫图”,如果你是指我有意做出些痕迹引导观众误入歧途的话。用风景前背向观众的形象,我是想讨论在我们这个时代人和风景是什么关系。我的观点是,我们把“自然”看做空闲时间可以做的事情中的一种,就像博物馆一样,而这是我在这个系列作品想摆脱掉的一个主题。也就是说,摆脱那种自我指向性的东西,真实地回归到世界当中。我那时就想不再画建筑了,除非我找到另一种画建筑的方法。我问我自己,如果我把一个现在的城市居民画到自然风景中,从绘画上看会发生什么?开放的空间会不会和封闭的室内空间一样对画中人物发生作用?这些画的形式确实与浪漫主义画作类似——毕竟,我对我们头脑中储藏的那些画很着迷,这其中当然包括——特别是在德国——浪漫主义的遗产。今天来看,我觉得我画的有些风景和浪漫主义的东西过于相近了,这样就会迫使观者过于用艺术史的方式观看作品。在有些人眼里看来,这种艺术实验中有某种乡愁似的炫耀,其实根本不是这样。
《伴娘》是个伟大的作品,可惜我还没有机会看到原画。画的观念很吸引人,画一幅像巨大镜像一样的画,而不是一幅像是透过窗子看到的情景。这就总结了过去150年里油画的整个话语。《拖车》能让你联想到这个作品,这很有意思。从几个世纪以来生长的层层植被上抽出一条很长的主题线,我有时候挺喜欢这样的。这和用文化记忆的方式返回图画结构有点联系。在这份虚拟的档案中,委拉斯凯兹可能会被放在维加旁边,而某个日报上的一幅照片可能是德加那份档案中的第一个文件。它触及了这个问题,即什么样的记忆和我们的感知能力以及我们理解绘画的方式有关。
杰拉德·马特:我想谈谈另外一个在你作品的接受中经常被提及的问题:画中形象的孤立性。你曾经和德意志银行收藏会的塞巴斯蒂安·普罗伊斯(Sebastian Preuss)谈过这个问题,认为不应该把孤立和寂寞混淆。你还说,孤立可以说是一种独处,一种静下来聚精会神的机缘,在这个时刻,人会更接近自我。你是否认为自己的作品像一隅绿洲,独立于符号的喧嚣和糟扰的社会之外,给观众以沉思冥想的空间?当观众花了很长时间观看你的画,在画中寻找意义甚至故事情节后,最终找不到答案,被孤零零地留在那里对着画作发呆;而这时,在这种孤立的状态下,他们也许会开始寻找自我,是这样吗?另一种可能是,画中人物的那种状态可以解读为对我们社会中一个主要现象的反思,即政府和商业机制会在人们身上贴上“人力资源”的标签,用剥夺个体任何责任的方式赋予他所谓自由。这两种阐释都与社会利益或者甚至是社会义务相关。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你觉得你的创作会不会有我上面说的那种作用?甚至展示悬挂你作品的地方也是值得玩味的,比如像德意志银行这么一个全球性游戏者的收藏会里。
蒂姆·艾特尔:政府是行政机构,所以可能永远会用很功利的视角去看待社会个体,比如把人们看做税收的来源,潜在的危险,或者选举人之类。政府需要每个社会个体,但它只想行使自己的管控职责,不参与或者被一些自身范围之外的要求缠扰。这看起来是行政机构的本质,是贯穿卡夫卡一生的主题。
我自己当然关注社会,但艺术肯定无法纠正社会的错误,要谈教育的话,一定有比艺术更好的办法。艺术总是一些大公司手中的玩物,被用来提高它们的形象,这是一种不能调和的矛盾,毕竟很多项目没有这些资金上的支持就无法完成。公司和政府用艺术来维护自由、开放以及批判精神,德意志银行本质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没有不同。也就是说,无论多么艰深的艺术,也无法避免被用来当作遮羞布。
我创作时,要观察社会中的现象。让我感兴趣的是习俗的力量和时尚带给人的负荷,它们属于集体主义机制,个体几乎很难避免。与之保持距离的有效办法应该是独处(孤立)。
大城市中的离群索居、喧嚣中独立的一隅,这是我的关注所在,因为只有在这里,个体性和集体性才会发生剧烈地碰撞。个体要时刻注意保持平衡,太少了你就是个无趣的人,太多了,就又成了游离社会之外的怪胎。我这里说的不是那些靠奇装异服进行所谓反抗的亚文化,因为它和中产阶级的集体主义比起来没有什么不同。
我每天的大部分时间是和自己独处,工作室里也没雇助手。有时候这纯粹是折磨自己,但这很重要,因为我需要时间去静下心来专注于观念,清空脑子来思考作品。这种体验就藏在你刚才征引我的话的后面:独处是洞察自身思考的有效方法。
尽管我们还会问到底这个自我是不是真的就是自我。我读到一些神经学研究,认为人的头脑中找不到一个所谓稳定的支撑思考活动的核体。这些研究认为,自我是一个过程,自我身份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临时状态,取决于成千上万种因素。如果认为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能感知到自身的特性,这简直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谎言。
我经常怀疑我所作的事情有何意义所在,绘画完全是一个自私的职业,能填充我的生活,却对任何他人没有好处。如果你告诉我说,艺术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帮助塑造我们自身和推动批判意识,或者更崇高一点,人文主义永不该放弃:这都对我没用。但我接着就想,我还能做点别的吗?这问题马上就解决了。
杰拉德·马特:有关身份和自我的问题已经被技术的可复制性和绘画的可变更性重置。上世纪80年代以来,媒介的视觉世界在造型绘画中扮演了极具影响力的角色。比如新莱比锡学派的艺术家,这也是你的出身背景。阿诺·林克(Arno Rink),你当时的老师,被看作第一位拥护“现实主义”绘画及其对媒介图像反思作用的人物。你和林克是什么样的关系,你从他那学到了什么?
蒂姆·艾特尔:在我参加林克那个班之前,有各种传言说他这个人有多严格、多冷血。第一次上课的时候,他好像是要有意证明这一点似的,跟我们说:“不干活的人我就扔出去!”但实际上不是这样。他把你当同事一样对待,把自己的创作放在后台,经常很公开而不教条地询问学生的目标是什么。他会不断地问、不断地去证实,直到我们身上最顽固的自我欺骗成分崩溃掉。这就是我从他身上学到的,一种自我批判的能力。
杰拉德·马特:你一般从哪里获得创作的主题?据我说知,你会拍很多照片,以备以后使用。你会不会有意出门去寻找主题?而且尽管你经常出门在外,但作品中很少有那种异域风情的东西。你会不会让自己和某些文化狩猎场主动隔开?
蒂姆·艾特尔:这是一定的。我只能说说我自己的文化经验,其他东西就纯粹是臆测了。我到了一个新地方,一般要用很长时间才能找到主题。原因在于我首先要做的是先把这个地方表面上有代表性的东西剔除出去。这种东西可能人人都知道,比如你第一次到纽约,面对各种高楼大厦、古怪的事情会不知所措,有些视觉编码会造成你的误读。只有多呆上一段时间,才能摆脱这种直接性的经验干预。至少从我来说,这要很长一段时间。我很少专门出去找主题,一般我都是带着一个照相机在身边。照片就像草图一样,我从它们中间截取一些我想要的东西用到作品里。
杰拉德·马特:参观你工作室的时候,我看到了很多大小形制不同的作品。作品的大小对你来说重要吗?
蒂姆·艾特尔:大一点的作品所产生的效果和小的完全不同。大的作品直接面对你的身体,给你一种很直接的空间体验。你可以后退、靠近它或者钻进去,这就像纽曼(Barnett Newman)认为对他那些大型纪念碑式的作品来说,能让观者这样做是最理想的。这是一种身体上的强迫感,就像弗朗西斯·培根的三联画。而小的作品会迫使你缩短和它的观看距离,进入到某种静默的对话中。这是一种更为私人的交流形式,因此绘画语言上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
杰拉德·马特:你的工作室里摆着一幅你还在画的作品,画的是两个卡在一起的购物车。你跟我解释说想画的是临时的橱柜或者住所。很明显你画的是你走在洛杉矶市中心街上时看到的一些无家可归的人所用的购物车。为什么选这个主题?
蒂姆·艾特尔:那确实是一两个无家可归的人的东西。我决定把它用作主题是件很自发的事情。首先让我感兴趣的是购物车外形的感觉,又笨又重的,流浪汉颇费用心地把各种袋子乱堆在里面。我问我自己,这些盒子、袋子堆在一起有没有顺序?我会觉得新的东西会一层层的堆在外面或者所有东西的最上面,而车里面的东西会被压碎,或者就永远埋在那里。如果给这个车做个切面,我们就能发现时间的痕迹,就像树的年轮一样。我后来越来越觉得这是个象征,可能象征了都市生活的存在状态,这甚至不必要和无家可归的人联系在一起,对他们来说,这幅画就是把一些可移动的财产堆起来,是一堆有用的东西。
杰拉德·马特:你在洛杉矶、纽约呆了很长时间,后来搬到了柏林。“吃住工作在柏林”是不是成了今天艺术家的座右铭?
蒂姆·艾特尔:我之前在柏林生活过。对艺术家来说,柏林是个非常有益的地方。原因大家都知道:空房子很多,房租低,开放而不断成长的国际艺术舞台……在纽约生活更艰难,也贵得多,但强度很大。比起来,生活在柏林还是很惬意的。
杰拉德·马特:你最近在做什么?
蒂姆·艾特尔:在画一幅很高很大的画,你来参观我工作室的时候我就在做这个,画的是一个有点失去纵向平衡的废弃桶。桶上面露出不少蓝色垃圾袋,一群鸽子落在上面,它们的比例和桶比起来显得有点大。无人之地上的一群鸽子,这是不是又和霍普有点关系了?
(杰拉德·马特(Gerald Matt)对话蒂姆·艾特尔,2007年8月。2008年维也纳艺术大厅举办展览“西方汽车旅馆——爱德华·霍普与当代艺术”Western Motel. Edward Hopper and Contempary Art)
蒂姆·艾特尔(Tim Eitel),1971年生于莱昂贝格,工作生活于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