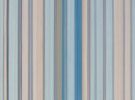2010年5月,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靳之林先生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大型个人画展,第一次全面展出了他六十余年来对油画的追求和探索。在靳之林的画笔下,满眼皆是对自然的崇敬感喟,“参赞天地之化育”是他所有绘画的母题。
靳之林始终对大自然充满激情,大自然的魔力使他对其他题材无法产生动笔的冲动,他只愿对景写生,甚至不能再在画室中重绘一幅他画过的场景,他的作品几乎全部是外光写生,记录下来的是对生命和万物生长的歌颂。
玉米地是靳之林喜欢的题材。画面中,玉米叶旋转生发,蓬勃生长以通天通阳,叶子颜色深绿,分明已是生命力生长到最旺盛期,却似乎仍旧带着种子从土层中钻出时的锐利和坚韧,向着高远的天空尽力伸展。画家被这种生命的状态感动,他把玉米生长作为“生生观”的精神写照,用他从本原文化中求索的符号,幻化成“S”形变化的线条,跳跃地涂抹在画面上,他把自己的生命激情和玉米地的顽强生长凝结在一起,讴歌这种生命的力度和张扬。
黄河也是靳之林喜爱的主题。仅仅乾坤湾这一段,他就画了一百多幅。黄河流经乾坤湾时,水流遭遇大山,无法通达,黄河水就一次次的冲击、改道,把河道拧成了九曲十八弯,终究奔流向前。靳之林的个人性格也如此百折不挠,执著求索民间文化的精髓,“虽死而吾往之”。靳之林在考察秦直道的途中心脏病发作,差点送命。但好转后他再赴征程。在去苗寨考察时,他的身上还插着体外胆管导流管,冒着生命危险依然不管不顾地研究,因此,他对黄河的精神格外情有独钟,在创作时完全是一种忘我的状态,用中国国画家使用的毛笔和油画刮刀结合,按照直觉的指引去作画。画时根本不去琢磨技法,只顾把颜色往画布上涂抹。那一刻,绘画就是生命狂热的激情。我画故我在,魂魄与自然融为一体。
对靳之林来说,激情永远比技法重要,技法在他学画的阶段以及早期创作中就已经解决。
靳之林自幼对色彩有着敏锐地感觉,无师自通地对光线和色彩有着本性的理解,在小学读书时,曾经观察爬山虎叶子在阳光中神秘的色彩变化,画出了一幅难忘的色彩写生。升学进入北平市立师范读书后,他一度成为当时国画名家吴镜汀的私淑弟子,在吴先生指导下临摹王石谷,至今还保留了一件当年临摹王石谷的《蹊山行旅》图。靳之林还担任了学校“冬青书画研究会”第二任会长,在李智超先生指导下临摹石涛,以至沈石田、黄子久、李成、范宽等人的中国山水画三百多幅,三年临摹的硬功夫,使他基本掌握了中国画的用笔要求,墨色晕染技法,对中国画中的笔墨韵味、意趣有了个人体悟,但是对光影效果的迷恋使他最终选择了成为一个油画家。
1947年夏,靳之林考入国立北平艺专美术系西画组,开始学习油画。徐悲鸿、吴作人、王式廓、董希文等先生是他的老师。在校期间的作品就曾受到徐悲鸿先生的表扬,说他作品的颜色“响当当”。时任院长的徐悲鸿先生重视油画进入中国本土后的民族化,砍掉一半的油画课让学生去学国画。安排李可染教临摹《八十七神仙卷》,蒋兆和教人物,叶浅予教速写,田世光教宋徽宗工笔重彩。徐悲鸿先生还亲自邀请齐白石先生给油画科学生上课。这些国画大家的授课使靳之林对中国画的素养得以升华,对中国画的理解也在靳之林的画笔下有所呈现。六十年来,靳之林的油画作品中始终可以看到有中国毛笔的笔法痕迹。
作为画家,靳之林和同时代的其他油画家一样,在“文革”前创作出了许多表现新中国现实主义作品。1954年夏天创作的《太行山村的早晨》参加了全国青年美展。同期完成的速写《我们建社批准了》在北京日报头版发表。1955年完成《罗盛教》,1956年创作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妇女间棉苗》、《打机井》。创作的作品受到艺术界的好评,技法表现已经熟练。1961年,他完成了早期代表作品《南泥湾》,展现了他对于多人物,大场景的画面控制能力和表现能力。十年动乱受尽磨难没有大的创作问世,但他创造机会,画了一批在“五七干校”的工作学习生活,这个阶段的作品也是他对自己人生历程的记录。他的命运在1973年发生了转折,那一年,他终于落户到了心中的圣地——延安。
“悲鸿恩师的《箫声》,引我进入艺术的殿堂;古元同志的版画《菜圃》,送我到了黄土高原之乡。陕北窑洞的老大娘,给我两把金钥匙:一把叫‘生生’,一把叫‘阴阳’,打开了民族本源文化的宝藏,打开了人类本源文化的宝藏。”这是靳之林对自己艺术之路的总结。
靳之林的人生经历是分段式的。学画之后留校任教,之后奔赴东北支援东三省的建设。文革十年,和许多画家一样不能作画。文革后期迁户到延安,在延安群艺馆工作时,进行民间剪纸普查,无意中让他发现了一个全新的美学体系,他从此开始投身到对中国民间文化的考察和挖掘工作中,研究中国民间美术的传承方式和体系,并将之带入中国高等美术教育的课堂。他从小美术纯美术的校园中走出来,走到广阔的民间去,走进大美术和大文化,挖掘中国民间美术中的大美,找寻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进而追寻人类文化的基因密码,作为实证考察的践行者写出了几十万字的考察报告和研究成果,他的著述在多个国家翻译出版,把中国文化对人类文化的贡献推而广之。这个时期,他随手的速写记录没有间断,但几乎没有油画作品问世。1987年靳之林调回母校担任民间美术系教授,1987年到1997年,他主要进行民间美术的研究和教学活动,不遗余力地向世界推广中国的本原文化精华。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靳之林的创作激情被激发,又重拾画笔。他发现自己对于这个时代的感情只有通过画笔才能抒发。他走遍陕北,画情画景,从此进入绘画创作的盛期。靳之林每做一事必全心投入,因此在考古、民俗学、文化学、美术创作方面都有成果,这些成果在靳之林的血液中融会贯通,汇聚成靳之林独特的艺术人生和艺术面貌。
胡适曾有书云:“文学史上有一个逃不了的公式。文学的新方式都是出于民间的。久而久之,文人学士受了民间文学的影响,采用这种新体裁来做他们的文艺作品。文人的参加自有他的好处:浅薄的内容变丰富了,幼稚的技术变高明了,平凡的意境变高超了。但文人把这种新体裁学到手之后,劣等的文人便来模仿;模仿的结果,往往学得了形式上的技术,而丢掉了创作的精神。天才堕落而为匠手,创作堕落而为机械。生气剥丧完了,只剩下一点小技巧,一堆烂书袋,一套烂调子!于是这种文学方式的命运便完结了,文学的生命又须另向民间去寻新方向发展了。”
古今中外都有例证,艺术家从民间美术中感应到原始的,新鲜的东西,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启发使自己的创作得到升华。靳之林从发现、感悟民间艺术,到扑入民间艺术全身心地探究,是一种主动地,淘宝式地发掘吸收,恰好从美术史的角度对胡适观点提供了佐证。
靳之林把他对于本源文化的理解,融入了血液,由此开创了油画四条屏的探索,把他对于自然的热爱,抒发为对生命绽放的歌颂。他画各种盛开的花卉,以及“寒来暑往”四时的变迁景观。靳之林在油画里用笔很自然,笔未到气已相接,每下一笔和气要连接、贯通,他在画荷花时,感觉普通油画尺幅不足以贯气,荷秆延伸,接天接地,无意中画幅尺寸成了国画中四尺整纸的条幅。靳之林的国画素养为自己的油画创作打开了新天地。
靳之林喜爱并擅长画雪景,所绘的雪景是天地人“三才”的浑然融合,直觉的传达通过狂放的笔触画面疏泄问世,是天人合一的自然象征。
靳之林1997年之后的作品,可以找到浓重的中国文化印迹,这不能不说是他对中国本原文化的研究滋养了他的心怀。他更加关注体现中国这块土地上自然观的题材。无论是黄河还是玉米地,或是雪景,都是对大自然的歌颂,是豪放的对大自然生生不息精神的赞美。画面的景象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观物取象”,而是“心象”寄寓于眼睛所见之形象,把对自然的理解凝固在画面上,用符号性的线条组成画面,把“天人合一”的中国山水画观念运用到油画创作中,这是对中国人的自然观的传达,一种激情和精神的记录,一种“激情大写意”的画风。
靳之林有中国式的浪漫主义情怀。他激情豪放,喜欢大山大水全景式的风景。他在画布上纵横捭阖,疾风暴雨般地倾注感情,而又有足够控制画面的能力。他精力充沛,遇事奋不顾身地投入,他善用写生捕捉一切自然之美带给他的冲动。当他拿起画笔时,就是在纵情长啸,几十年来沉积在他胸中所有的文化积淀、浪漫情怀、不畏艰辛的本能化作激情喷涌而出,直到他完成心中的绘画表达。这种激情本能的释放与一般理智描绘对象的作品截然不同,带给观众的感动也不属于一个层面。很难用一种词汇说明这种绘画的含义,我把他称为“激情大写意”油画。
靳之林坚持不懈地探索和实践,给油画这个外来画种增加了独特的面貌,也造就了他独特的艺术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