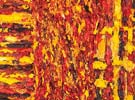记者:实验水墨这一块在广东的发展与岭南画派的发展有没有关系?
王璜生:这是两回事。岭南画派还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岭南画派最关键一点,他们倡导了一种精神,变革的精神,中西融合的精神。也做了一些具体的实践。岭南画派一直备受争议。特别在早期。争议是由于他们中西合璧的口号究竟成不成立,还有像潘年寿提出的拉开距离等。关键是他们的具体实践能令人信服,当时整个社会的欣赏习惯,对文化的定位使大家对中西合璧的观点还是持有难以接受和认同的感觉。因为他们的实践还没有达到令人信服。这也是一个问题。应该讲,在广东,很多行内人提到岭南画派,心情是非常复杂的。既有应该去倡导的感觉,也有因为这个品牌不是那么靓,备受争议。这个品牌也越来越政治化、世俗化。有些人虽然可能是岭南画派,或被外人认为是岭南画派,但他们不愿意承认。岭南画派如果说和水墨有关系,那可能是艺术精神的关系,大家都追求变革。但如果从形式上讲,或从文化的处发点讲,是比较远的。岭南已经变成不是文化内涵。而是高度政治化、世俗化、商品化的代名词。
记者:广东当代艺术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广东艺术家创作早期在广东,然后会有北漂移民的倾向,或出国。像王度、李竟、曹斐后来也都离开了广州。这种现象是不是和整个市场有关系?王璜生:这种现象是非常正常的。人来人往、进进出出也很正常。四川、上海等也是这样的现象。有出也有进。其实这么多年像走出去的,谈到王度、杨诘苍或曹斐,现在的比如陈少雄在北京有工作室。我觉得这都很正常。也有很多艺术家从北方过来,比如湖北群体,杨国新、方少华等等,都是从那边来的。我觉得这种现象很正常。如果再追问一下艺术生态问题来讲,从好的一方面来讲,都是比较个体化的。大家该做什么做什么。没有一个地方像798那样具有号召力聚集一起,艺术家的工作室什么的都分布在各个地方。还有一点就是,艺术家的整个心态,还是比较宽松。可能市场的问题没有那么迫切。在北京,在798,某些人很红,市场上闪光的东西很多,你必须抓住这些闪光。但广东因为没有太多闪光,艺术家心态上挺有意思。但是如果从不好的地方讲,广东这里还是缺乏一个彼此呼应的气氛。艺术缺乏一种联合起来、共同创作的气氛,这里的感觉比较自我。第二,这里的市场没有像北方,上海北京那么集中,那么艺术家真正的一种生存、更合理的一种生存方式受到挑找。艺术家获得更大的一种空间、利益、名堂,那么他必须走出去。另一个就是,学术探讨的氛围带有两极分化。一边很世俗化和政治化的占据主流地位。另一方面有一种学术化探讨的东西。这方面的影响力、力度等,都是相当有限的。这种两极分化的过程中也很难形成一种比较好的学术氛围吧。
记者:广州美术馆和广州美院在生态上起到什么作用?
王璜生:广东美术馆我比较熟悉。从建馆以来,我们一直都在坚持文化理想和文化学术的一种推进。这里面包含了一种对美术史问题的学术态度。我们如果从学术的角度去挖掘和整理美术史上的一些现象和个人、作品、资料、事件等等,是比较认真有序的去做的,而不是东打一枪、西打一枪。对地方美术史的梳理,我们一直保持着独立的学术态度,不受其他外力如政治、经济的左右,而是按照学术的标准、文化的理想和态度来做这样的事。我们做了些广东很重要的艺术家的展览。谭华牧、符罗飞、冯钢百、赵兽等在现在美术史上都是非常重要的艺术家,但很长时间被忽略。这是我们所做的。包括一些事件:西北文物考察团的历史事件研究,30年代广东前卫艺术家和上海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时代的美术,都是从美术史研究的空间来开展的。
另一方面就是,对当代艺术的推动:当代艺术是一种进入当下活动表征的艺术。总体上它是集中地反映了当代文化的方方面面,应抓住这点。从展览、收藏、资料的汇集等一些列工作是比较全面的。包括对公众的当代艺术的教育和意识的建立,我们是比较重视,全方位的去推动的。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我们一方面是推动着这工作,一方面是在研究整个社会发展的审美,对文化艺术的需求,在这里面做出研究。我们发现,社会是在不断地变化,对当代艺术的感觉和需求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化。很多公众会从当代艺术这样的方式去获得一种新的认知社会、启发创造力、新的思维的东西。
在我们所做的当代艺术活动里面,一方面是在推动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是在启迪公众文化的一种新思想、新方式。这是整个社会共同需要的。需要新的方式和理想。因此,我们觉得我们的努力还是值得的。在广东,大家有目共睹。广东美术馆成立10多年了,毫不讳言的说,是有很大变化的。包括这次广州三年展,题目这么晦涩,当代艺术这么难懂。但观众如潮,普通观众买票来三、四次,发现里面有东西,有意思。这是社会一个很复杂、很多元的现象。艺术应该是一个鼓励自由创造的精神、鼓励公众自由发挥、激发自身创造力的方式。而不是说,他们(观众)来了后按照上面的规定,按照政府的要求,接受教育,问这件东西要告诉我们什么。这不是艺术的目的。艺术是要激发公众一种自信和创造理念。
记者:广东美术馆在办这样的展览会不会因为尺度问题通不过审查?
王璜生:在尺度方面我们都有一定的把握。不会有比如说颠覆国家、过于血腥的东西。尺度的问也是值得好好研究的。我发现,无非就是:一,你作为一个文化的活动者,你自己心中有一个尺度,然后这尺度不是说始终将政府的尺度放在你尺度里面,或者说政府也许还没有这尺度,也许你已经像这东西先有这个尺度。好像前些年有个说法,政府不同意举办装置展览,但是我们没有得到政府明文规定不能有装置展,装置展是一种形式而已,就像雕塑一样,并不是说它就是一个反动的东西.上面也没有规定,但我们文化的执行者先设置了一个不要犯忌的心态。作为一个文化执行者来讲,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尺度。第二,是政府来管理的时候,他们也应该懂得文化的尺度在哪里,而不是随便望文生义,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代表政府来诠释。经常会碰上这样的问题。但是这问题也是能够通过各种方式来解决的。
记者:像三年展这样大型的当代艺术展会不会遇到其他的困难?
王璜生:这些问题其实刚才都回答了。如果说还有什么,就是经济的困难,因为像这么大型的展览的举办,对一个城市和区域来讲,是文化的大事,它既能够提升文化区域的品格,同时也能提高城市的市民的文化素质,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一种新的东西。作为一种国际上的双年展、三年展,很多都是地方政府或国家在支持为主的。做得好,包括旅游业的提升,市民发现新的生活内容,等等。是政府要为这个区域做什么。三年展最大困难在经济上,更多是通过自身的努力去获得。广州三年展所做的规模和造成的国际影响很大。这一届也被业界评为全世界最好的三年展。但如果我们有更多的资金来源,也不会做得这么辛苦,也会做得更好。<BR>
记者:三年展有没有采取一些商业的操作模式?上海双年展和瑞士UBS银行签了赞助协议。
王璜生:不是瑞士银行,是瑞士的一家叫“嘉盛莱宝”的银行。更多的是政府层面来完成的。政府注入了很大的资金。很明显,“嘉盛莱宝”是冲着上海来的。上海是金融的窗口。“嘉盛莱宝”要打进上海,在上海立足脚。要不谁知道“嘉盛莱宝”?
记者:三年展的策展思路和上海双年展有没有比较大的区别?
王璜生:其实从策划展览的角度上来讲,从程序、出发点、工作方式上来讲,没有太大的区别和不同。都是选策展人,和策展人一块工作,选艺术家,学术定位,研讨会,展览,呈现等等,没有太大的不同。如果有不同就是人的不同。因为各个群体定位的目标和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在做的过程中,所选的主题和艺术家会不一样,呈现出来的东西会不一样。
记者:您有没有看今年上海双年展?在艺术专业领域大家都觉得此次双年展诟病非常多。
王璜生:我看了。其实广州三年展争论也很大。但我挺自信广州的三年展,“与后殖民说再见”能够成立与否且不论,但能够引起这么大的关注,也是很有意义的。大家能够去思考“后殖民”究竟是什么,大家是否生活在后殖民的语境里面,我们能否和后殖民说再见等。这些问题能够去思考,就会比较有意思。我觉得做这么大的投入和精力,必须对当下的文化问题提出问题。或者切入当下最前沿的文化。这样才能激励艺术家和公众大家共同思考。而不是像旅游节一样,像观光一样,大家看看就完了。如果只是做一个艺术节或旅游节,那么三年展怎么做都比不过一个旅游节,观众再多,都比不过一个旅游节。三年展要做什么?许江的讲法就是:双年展的定位首先就是为一群能够独立思考的文化人提供一种思考和表达的场所。我觉得我是坚持这样一种立场。首先,三年展既然投入这么大,又是一群文化人在做,首先应该是一种前沿文化的思考,大家来共同思考该怎么做。然后,三年展的成功在于业界、艺术家、共同的文化人去关注它,说好说坏都行,得到好的评价当然非常好。第三才是公众,有更多、更好的公众参与进来当然更好。但如果说没有,其实并不是最重要。公众再多,如果非专业,那么对这样一种展览的专业性、挑战性是没有太大联系的。当然,我们的做法是努力的在我们学术主题方面有一种出发点。在公众的宣传点方面我们也去做。
记者:接下来还有什么大的展览计划?
王璜生:今年底会有一个让公众参与的“欧洲绘画精品展”,当代艺术方面暂时没有。但有一个对广东民间美术生态考察的展览。这个展览也用了比较新的方式,包括录像、照相、访谈、日记、实物、影像、资料,综合性去呈现广东当下民间美术的生态。这次是做广东东部,明年会做中部和西部,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进行考察,这也是我们工作的一个方面。我们并不是完全做当代的。
记者:广东的市场的流动性问题?
王璜生:总体上感觉,广东的画廊业目前还是举步维艰,也不太多。很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机构或参与的区域能够使大家聚在一块,形成相对比较有操作性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