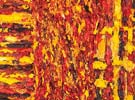倪:回到画面本身呢?柠檬黄和各种荧光色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黄:这些颜色一直都有,它们明亮,新鲜,他们在我的画面里由来已久,最初像是闯入者,随后慢慢变得舍不得离开了。
倪:你的很多作品中都描绘了人或者人体的形象,在我的理解,描绘特定环境中人的符号是表象的,你其实是希望作品中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黄:那些肢体,面容和零散的器官,都是以解剖方式呈现的,是叫做“人”的动物体在自然世界前的对峙,我感兴趣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动物性的人与文明角色的扮演者之间的关系。
倪:另外只有熟悉你的朋友才知道,你画面中的人物形象基本上都是和你生活密切相关的那两三个人,你在画面中反反复复描绘他们,有时候甚至像是一种剖析,对于这种超常规的表述方式,有什么更深的意义?
黄:他们是与我生命直接关联的、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两个人。我对他们的描绘和剖析是别无选择的。另外,每一张画,从挑选画布,定制内框,绷布上框,到反复几十遍的刮刷基底,打磨,都渗透着我们的合力劳动。而绘画以及围绕着绘画劳动展开的生活,令我们的心灵得以栖息其中。在我的画《栖息地》中,你能看到我个人生活的碎片。
倪:我觉得现在很多人看画往往有一个误区,对于一幅画,大家关注的兴趣往往停留在一些所谓的“概念”,而忽略绘画本身的很多特性,比如绘画语言,技法之类的东西,这也误导了很多艺术家在进行创作过多关注于一个小的“想法”而忽略了承载这些好想法的好表达。事实上我在阅读你的作品时,绘画语言传递出来的抽象情绪往往比一个图像的简单概念要来的生动具体。或者说,单从概念上阅读你的作品,是表面空泛的,我能看到你其实在绘画里面有很多用心良苦的东西。
黄:其实只是这些绘画的特性,暂时不再吸引他们了,但仍强烈的、而且越来越吸引我。艺术家群体里有不少“服务型艺术家”,藏家想听相声,他们就抖包袱;藏家想做传销,他们就要学习洗脑。我和他们的差别在于,我缺乏服务意识,我面对的只有具体的视觉接受和处置器官。还有,我会给特别眷恋我绘画的人们,准备他们独享的晚餐,那就是你所说的“用心良苦的东西”,我叫它绘画的潜语言。
倪:我的理解是绘画语言本身就是潜在的,就好比好的具象绘画,最终传递的往往是抽象的信息。比如挥洒、刻画、流淌等等,都是很准确的信息。我多年来始终很怀疑“人民艺术家”、“雅俗共赏”这些词,就像你说的,这些词里面好像隐含着一种“服务意识”,我始终觉得好的艺术就是小众的,“曲高和寡”是一个显示的词汇,其实同样是画画的人,对你说的“潜语言”有敏感度的却很少。
黄:我的画不属于快餐视觉,因此需要花费时间和心思的人们,这是个问题但又不是个问题。艺术品对观众没有门槛,但总有人进来、跨进来和不进来,我更倾向于艺术和他的欣赏者是相互选择,自由恋爱的。
倪:我知道你显然是一个在画面上强调精确控制力的艺术家,甚至连一些表面上看来的偶然性效果都是你有意为之的。你觉得这和性格有没有关系?
黄:这是个气质性的问题,像强迫症,它每次都给作品的拍摄和印刷过程带来无限的纠结和烦恼,很难完美。
倪:你在表达过程中顺畅吗?目前在绘画的技法语言上你有没有某方面的瓶颈?
黄:是的,总有不顺畅的时候,就是不能淋漓尽致或者对误读的顾虑。我认为技法瓶颈其实不存在。艺术家只有想画的时候和不想画的时候。不想画的时候偏又不得要画,才有了“瓶颈”,有了愿望,自然就有了方法。
倪:你有没有想过尝试绘画以外的语言媒介?
黄:想过装置,觉得有意思,画过几个草图,没机会完成。
倪:你的那张《自由》给我很深的印象。那是很好的一张画,是你度假的岛吗?
黄:“改变中的生命史”展览完成之后,朋友邀请我去巴厘岛度假,在飞机上俯瞰海洋,让我坚定的想完成这样一张大画,让它和之前的另外一幅大画《饲虎图》相呼应。空中俯瞰的岛屿,在2004年关于性与隐秘私生活的系列作品《日志》中就出现过,之后,2010年的《肖像》里,它还在一幅解剖后的侧面人像的背景中出现过。
倪:里面好像有一段藏文。
黄:对,那可不是一句经文或咒语,他是我喜爱的流行乐歌手周杰伦在《稻香》的一句歌词: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其实人们很难了解藏文的意思,他们只看见喜马拉雅山区的古老文字,出现在辽阔汪洋中的岛屿上。
倪:那么,你怎样理解“自由”?
黄:古拉丁语里,“自由”( Liberta )的含义是从束缚中解放出来。在古希腊古罗马时候,“自由”与“解放”同义。对生命个体而言,这绝对是一种致命的享受。
倪:虽然前面谈到了你近年来创作上的一些转变,但这些恰恰是你在两个不同展览中以一贯制的东西。
黄:是的,线索一直非常连贯而且清晰,如同河流与血液的流淌。
倪:我和艺术家聊天,在最后我往往最想问的问题是:在目前阶段,你觉得你自己面对的比较大的问题(或困难)都有哪些?
黄:经济问题,我快要生活不下去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