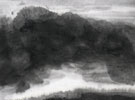许江参展作品《大北京·大城楼之一》
早报:您要做的第二件事情,是出一套文献性的丛书,详实地梳理中国当代艺术前后的历史。这段历史的话语权,其实大家都已经在争夺了。您是要书写权威的历史?
罗中立:这套丛书会以国家课题的形式操作。现在各种机构、民间个人,都在书写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产生了很多成果。但正因为大家都在做这个事情,所以需要更权威、更客观,需要超越局部、超越市场甚至是集团利益的历史。我们还将邀请现在活跃的这些批评家、理论家来写,可能要花三五年时间,但会有专门的委员会审核,有学术约束的机制。我们所写的这个,不能说是正史,因为别人写的也并不是野史。
早报:难度最大的应该是第三件事情,建立一座中国当代艺术馆。目前这个事情进行得怎样了?
罗中立:我争取要在北京建立一座中国的当代美术馆。中国当代艺术,目前为止只在民间、在机构、在市场、在海外,而不在美术馆。中国的美术馆系统是不完整的,我们需要建立自己的蓬皮杜、古根海姆。
有自己的戏台,大家才能轮番上台表演,才能做很多有关当代艺术的事情,当代艺术才能算是有了美术馆根基。我跟当代艺术院特聘的艺术家们都谈过,他们都很愿意拿出自己的作品捐给未来的这个当代艺术馆。艺术家作为个体,都是有些自由散漫的,但在这种时候,其实都很热血。
我之所以感觉到,建立中国当代美术馆的时机已经成熟,是因为我当了十三年的人大代表,今年第一次听到总理报告中有相当大的篇幅提到文化作为一个国家最终竞争力的内容。接下来,我要去人大提案、争取立项、游说各个部门和人。
困难在于,国家意识形态和当代艺术之间还有一些无法兼容的地方,另外拿到土地和资金也会困难重重。推动此事,也需要媒体一起宣传造势。
早报:您在开幕发言中说,体制和想做的事情之间总有矛盾,由此深感体制改革的必要。和体制合作让你感到很痛苦?
罗中立:总会有一些内耗。当艺术类院校扩招、艺术专业报考很火暴的时候,每一个艺术院校的院长都成了房地产老板,忙着和城建、规划部门打交道,分散了很多精力。在这个特殊的时代里,在体制内做一些事情有非常大的难度。我同意出任中国当代艺术院院长,跟当初以一个普通教师出任川美院长一样,考虑了很长时间才接招。
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的教育背景、思维方式的关系,总有一种使命感,想要为中国艺术做点事情。到了这个年龄,背上了这么多的名分,以我的精力,做一个开局的人就可以了。那套书也好,建立中国当代美术馆也好,三五年时间是我自己设置的一个时间期限。
这三件大事办完、三板斧抡完之后我就隐退,自己搞创作去。不管怎样,目前的行政工作下,画可以少画几张,但创作的状态不能丢掉。行政是暂时的,画画却是从小到大安身立命的所在。
早报:很多人质疑,成立中国当代艺术院,是对当代艺术家群体的招安、收编。您怎么看?对于特聘艺术家的名单也有质疑,认为这些人在市场和荣誉上赢家通吃,中国当代艺术已经是一个封闭的精英化的小圈子。您认为呢?
罗中立:招安,收编,这是不同角度的理解。艺术家身在机构里还是在民间,不是艺术标准。真正的标准在于,作品是不是具有前卫性、实验性。美协、作协都还有职称呢,我们的当代艺术院只是个名分,是荣誉性的,不发工资不分房子,大家都还是很愿意来。事实上,这可以说是一个当代艺术的国家队,以后将代表国家层面进行各种文化对话、艺术交流。
我相信,全世界所有的体育明星、娱乐明星都是在赢家通吃的,而大家并不知道,今天这些成功的艺术家,在艺术不被关注的时候都曾经穷困得差点饿死。
目前的这21位艺术家,只是我们特聘的首批艺术家。以后我们还会分批去聘请一些别的艺术家。这不是一个封闭的圈子,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为整个当代艺术领域赢得更大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