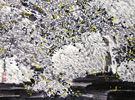一
2009年6月15日,由《文艺报》和盛大文学共同主办的“起点四作家作品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十多位文学评论家面对四位年轻的网络作家时不禁感慨,新一代网络文学作品与他们所熟悉的传统文学之间,如同隔着一道“巨大的裂谷”。张颐武甚至说,“中国新文学的想象力到70后就终结了。裂谷的这边是中国历史上最新的一代,他们的阅读空间就在网络,就是这些作品,传统文学的生命没有在后一代人得到延续”。由此,文学的结构会有根本性的变化,这种断裂造成的后果就是年轻人写年轻人读,中年人写中年人读。①类似的感慨,近些年在批评界时有所闻,它说出了一种批评的危机——在如何面对新的文学力量崛起这一现实面前,批评界不仅存在审美知识失效的状况,也有因思想贫乏而无力阐释新作品的困境。
这个困境,可能是批评面临的诸多危机中极为内在的危机,它关乎批评的专业精神和专业尊严。但是,批评界的这一危机,在过往的讨论中,往往会被置换成另外一些问题,比如,时代的浮躁,消费主义的盛行,批评道德的沦丧,人情与利益的作用,等等,仿佛只要这些外面的问题解决了,批评的状况就会好转。很少有人愿意去探讨批评作为一种专业的审美和阐释,它所面临的美学和思想上的饥饿。许多时候,批评的疲软是表现在它已无力阐释正在变化的文学世界,也不再肯定一种新的美学价值,而变成了某种理论或思潮的俘虏。翻译过罗杰·法约尔的《批评:方法与历史》一书的译者怀宇先生说:“文学批评在进入80年代以后越来越变成了与航天物理学和分子生物学同样特殊的一种‘科学’领域,……文学批评已经不是向读者介绍好书,或者为社会认定杰作,而是把作品当做验证分析方法和探索新的分析内容的基本素材。”②当文学批评过度依附于一些理论,一味地面对作品自言自语的时候,其实也是批评失去了阐释能力的一种表现,它所对应的正是批评主体的贫乏。我们或可回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虽然批评家也是多依赖西方的理论武器,但他们在应用一种理论时,还是以阐释文学为旨归,像南帆与符号学、吴亮与叙事学、朱大可与西方神学、陈晓明与后现代主义、戴锦华与女性主义、陈思和与民间理论之间的关系,都曾有效地为文学批评开辟新的路径,这和现在过度迷信理论的批评思潮,有着本质的不同。何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学批评日益演变成意识形态批评、道德批评、文化批评?正是因为批评家缺乏文学的解释力,以致在谈论文学问题的时候,只能从性别、种族、知识分子、消费文化等角度来谈,惟独不愿从文学立场来观察问题,审美感受的辨析更是成了稀有之物。为此,洪子诚曾质问:“如果文学批评已失去了它的质的规定性,而完全与文化批评、社会问题研究相混同,那么,文学批评是必要的吗?文学批评是否可能?”③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转型之后,却失去了解读文学的能力,它的背后,终究掩饰不了批评主体贫乏这一事实。
批评主体的这种空洞和贫乏,是造成批评日益庸俗和无能的根本原因。如果在批评家身上,能重新获得一种美的阐释力和灵魂的感召力,如果在他们的内心能站立起一种有力量的文学价值,并能向公众展示他们雄浑而有光彩的精神存在,时代的潮流算得了什么?人情和利益又算得了什么?批评的尊严并不会从天而降,它必须通过一种专业难度及其有效性的建立而获得。因此,批评主体的自我重建,是批评能否走出歧途的重点所在。“批评也是一种心灵的事业,它挖掘人类精神的内面,同时也关切生命丰富的情状和道德反省的勇气;真正的批评,是用一种生命体会另一种生命,用一个灵魂倾听另一个灵魂。假如抽离了生命的现场,批评只是一种知识生产或概念演绎,只是从批评对象中随意取证以完成对某种理论的膜拜,那它的死亡也就不值得同情了。”④
即便是当下被人热论的批评人格和批评道德的问题,同时关乎批评主体的重建。批评界何以存在着那么多平庸的、言不及义的文字,何以一边审讯别人一边又忙于吹捧那些毫无创造力的作品?一种审美的无能以及批评人格的破产是如何发生的?愤激地将之归结为批评家不够勇敢、不像个战士那样发力批判,或者把利益看作是批评人格溃败的主因,这些都不过是肤浅的看法,它并未触及到批评的内在特性。勇敢的人、敢于在自己的批评中横扫一切的,大有人在,甚至点开任何一个文学网站,都不乏那种把当下的文学贬得一文不值的人,但这样的冒失和意气,对文学和文学批评的自我完善有何益处?批评家作为以理解文学为业的专业人士,如果也仅满足于这种低水平的话语合唱,而无法向公众提供更复杂、更内在的文学感受,那同样是批评的失败。像那些断言文学已死、文学是垃圾的人,都是从一种整体主义的角度去描述一种文学的缺失,这对于解答具体的文学问题其实并无助益,因为真正有效的批评需要有一种诚恳的研究精神,必须阅读文本,才能洞察作家作品的真实局限。作为一个批评家,阐释有时比否定更为重要。而那些文学已死、文学垃圾论之类的言辞,之所以会引起巨大的关注,首先要反思的可能是一些媒体和读者的心理预期,他们总以为那种横扫一切的否定才是批评家的勇气。如果真是这样,“文革”期间早已把所有文学都否定了,新时期我们又何必一切都从头再来?一些人,惟恐别人记不住他的观点,总是想把话说绝,越专断越好,而知识分子读了一堆书,如果不懂什么叫节制、诚恳、知礼,不好好说话,也不懂在自己不知道的事情面前保持沉默,这难道不是另一种悲哀?批评精神的核心并不是比谁更勇敢,而是比谁能够在文学作品面前更能作出令人信服的专业解释。空谈几句口号,抽象地否定中国文学,这并不需要什么勇气,相比之下,我更愿意看到那些有理有据的分析文章。当我们在批判一种话语疲软的状况时,也要警惕一种话语暴力的崛起。
因此,理解批评存在的困境,和理解文学的困境是一致的。要确立文学批评的价值,首先是要确立文学的价值、相信文学的价值。批评精神的基本构成,是关于批评对文学的忠诚守护,对人的复杂性的认知。通过对文学和人的深刻理解,进而出示批评家自身关于世界和人性的个体真理,这依然是批评的核心价值。但在一个文学的精神性正在受到怀疑的时代,引起公众关注的,更多只是文学的消费和文学的丑闻。随着这些关于文学的笑谈的流行,写作也不再是严肃的灵魂冒险,不再捕捉生命力的话语闪电,也不再绘制创造力的隐秘图景,它仿佛是一种剩余的想象,充当生活中可有可无的点缀。面对公众对文学越来越盛大的揶揄和嘲讽,文学批评不仅没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叫人热爱文学,反而因为它的枯燥乏味,成了一些人远离文学的借口。这样一种蔑视文学的逻辑,在以会议、出版社和批评家为核心的图书宣传模式中,更是得到了证实。于是,文学逐渐走向衰败,文学批评也正沦为获取利益的工具。
以阐释、解读文学为基本伦理的文学批评,最终不仅不能唤醒别人对文学这一创造性的精神活动的珍视,还进一步恶化了文学环境,尤其是加剧了公众对文学及其从业者的不信任,这当然是批评的耻辱。另一方面,肆意贬损作家的劳动,含沙射影地攻击写作者的人格,无度地夸大一些毫无新意的作品,跟在网络或报刊后面为一些商业作品起哄,面对优秀作品的审美无能,把批评文章写得枯燥乏味或者人云亦云……所有这些症状,也在表明批评家已经无力肯定文学自身的价值,也不能把文学证明为认识人和世界的另外一种真理,那种个体的、隐秘的、不可替代的真理——人类世界一旦少了这个真理,人类的感受力和想象力就会缺少一个最为重要的容器。没有对文学价值的基本肯定,批评家如何开始自己的阐释工作?他根据什么标准来面对文学说话?
我冒昧揣测,很多文学批评家已不信文学。批评家不相信“真理”掌握在作家手里,不认为作家能够发现某种秘密,墨索里尼,总是有理,批评家也总是有理,社会的理、经济的理、文化的理,独无文学之理;批评活动不过是证明作家们多费一道手续地说出了批评家已知之事,而这常常在总体上构成了一份证据,证明批评家有理由和大家一道蔑视此时的文学,进而隐蔽地蔑视文学本身。⑤
需要恢复对文学本身的信仰。正是有了对文学的信,作家和批评家才有共同的精神背景,也才有对话的基础。从事文学的人却不信文学,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也普遍不爱这个时代——这或许是我们精神世界里最为奇怪的悖论之一了。作家不爱文学,自然也不再把写作当作是心灵的事业,甚至连把技艺活做得精细一些的耐心都丧失了,写作成了一种没有难度的自我表达,或者是面向商业社会的话语表演;批评家不爱文学,面对作品时就不会取谦逊和对话的态度,更不会以自己对文学的敬畏之情来影响那些对文学还怀有热情的人。为何文学这些年多流行黑暗的、绝望的、心狠手辣的写作,因为作家无所信;为何文学批评这些年来最受关注的总是那些夸张、躁狂、横扫一切的文字,也因为批评家无所信。无信则无立,无信也就不能从正面、积极的角度去肯定世界、发现美好。重新确立起对文学的信,其实就是相信这个世界还有值得肯定的价值,而文学也能充分分享这一价值。文学是对世界的发现,而文学批评是对文学真理的发现。发现、肯定、张扬一种价值,这能使文学和文学批评从一种自我贬损的恶性循环中跳脱出来,并在一个更大的精神世界里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