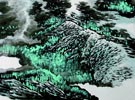我认为,现代民主社会的建立有两个基本前提:社会分工和社会分权——分工与社会运行机制相关,分权涉及言论自由和不同职业所拥有的权利。并且,现代多元文化系统的存在依赖于理论确证。即是说,现代多元文化系统与现代民主社会依赖于现代管理理论,其一方面诉诸于合理性——理论确证的必要性——即切实可行性,另一方面诉诸于现代法律所树立的合法性——即合乎正义性。在此思路下审视王南溟的“批评性艺术”,那就能消除很多普遍的误解。
王南溟的学说并不激进,其只不过顺应了文化转向的趋势。对于西洋人来讲已经成为基本制度范畴的东西如今才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努力的至高目标。王南溟的目的不是政治,因为他真正的目的是,为艺术寻求制度与法律的保障,这种保障的必要性不压于艺术审美主体建构的重要性。事实上,“社会、政治维度”、“艺术的社会维度”和“个体、自我维度”、“艺术的审美维度”并不是孰轻孰重的问题,其在当下中国是同等重要、同时面临的问题。王南溟的知识结构注定他会有所选择地致力于“社会、政治维度”、“艺术的社会维度”。而从根本上讲,这两个维度也不是绝然能分开的。什么是前卫?前卫的第一要义是征对问题,不管是文化问题、审美问题,还是社会问题。
格林伯格认为,“前卫艺术是伴随着威胁与挑战而生的”,“威胁在于,艺术的最高标准由于市场的日益侵蚀,已不再受制于有文化的精英们的趣味,而挑战则来自一个更为明确的事实,即精英艺术如果再不像400年前那样那样进行持久而激进的创新(或者改进)就难以维持下去”。很显然,“批评性艺术”也是伴随着威胁与挑战而生的,一边是泛滥的商业主义,另一边是知识分子话语的生锈。事实上,“批评性艺术”亦是一种新的历史批判和社会批判,其包括两类:历史文化分析的艺术和艺术的新闻批评。如王南溟论述的,“这两类艺术的表现来源是不同的,对历史文化分析的艺术来说,它有着如何从文化的深层结构的内部颠覆出来的观念力量,所以相对而言比较抽象,而且需要历史线索的了解;对艺术的新闻批评来说,就要看艺术家如何从社会现实中去定格一种问题,所以它又是一种提前的声音和对具体社会问题提问和批评”。我认为,“批评性艺术”(“更前卫艺术”)是一种永无休止的批判行为,批判精神便是它的前卫性,而正是“批判性”使它成为前卫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 当代艺术之后:本体论的式微
不承认文化、艺术如生物、科学技术般进化、发展而认可“也许艺术的一个奇妙之处就是它不总是像技术那样合逻辑地向前进步”的观点,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用现代主义时期所形成的艺术、审美标准审视它之后的文化、艺术走向或文化、艺术生态。因为人们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已发现,为标准的文化不是合理的文化,更不是健康的文化,真理并非一系列罗列的标准、规矩——尼采、杜尚的智慧就已经对为标准、规矩的文化发起过最猛烈的反击。格林伯格的看法是正确的,“标准通常至少晚于同时代最佳艺术整整一代之后才能建立”。与此同时,人们也习惯犯一种错误,将艺术、文化的发展看成是不断否定(诸如后现代否定现代、文艺复兴否定中世纪、后前卫艺术否定前卫艺术、更前卫艺术否定后前卫艺术)的过程,就像猴子扳苞谷一样。事实上,艺术审美主体的建构是现代主义时期所完成的工作,后现代时期转向了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我认为,人类的“视知觉”——艺术范式呈现的并不是线性的发展、取代——新的视知觉范式取代旧的视知觉范式或正确的视知觉范式取代不正确的视知觉范式,而视知觉范式呈现的是增加、拓展的姿态。就此而论,我认为在当下试图以一种艺术标准衡量人类行为或确立又一种艺术标准的做法是荒谬的。
用“本体论”——“认识论”、“唯物论”——“唯心论”等的方法论、思维方式检视当下文化、艺术已显得力不从心。艺术有没有一个本体?如果承认有——承认其经由现代主义艺术建立,那么我们就可以发问:“当下艺术”(不是当代艺术)的本体是什么?艺术的本体难道真是亘古不变的吗?如果仍然采用诸如本质——现象、形式——内容等的法则衡量、审视当下十分混乱的文化、艺术是否依然具有可行性?事实上,自杜尚起,传统的艺术的本体已经被打破的(或说传统艺术终结了它自身)、传统的艺术的本体已化为无数个碎片。这一变化让明智的人认识到的是,艺术所指的固定和艺术能指的无限拓宽以及由无限拓宽所引发的单个艺术形态的重建和多个艺术形态的并存。事实上,“批评性艺术”只是这其中碎小的一片。我认为,对杜尚之后所发生的艺术事实的探讨应有一个基本的逻辑情境——看到传统的艺术本体终结之后艺术所指的固定和艺术能指的无限拓宽。
艺术能指的无限拓宽可能导致泛艺术论,而不是必然产生泛艺术论。但是,艺术(确指艺术的能指)拓宽了,这是一个事实。这一事实构成了我们今天探讨艺术的背景、逻辑前提。我认为,当前重要的不是重构统一的艺术本体的问题,而是解决在艺术的所指固定、能指无限拓宽的前提下如何推进艺术的问题。艺术的拓宽必然引出两个问题:一个是“是不是”的问题,另一个是“有与无”的问题。也就是“艺术是什么”、“艺术不是什么”、“什么是艺术”、“什么不是艺术”问题和“什么样的艺术有价值”、“什么样的艺术无价值”问题。前一组问题指向“艺术”本体,即艺术能指的拓宽;后一组问题指向与前一组问题相匹配的价值评判系统。很显然,一组问题对应与之相匹配的价值评判系统,这已不是单纯本体的问题。我认为,在当下,艺术便是如此:所指固定,能指无限拓宽。而人们很难说所指、能指都指向本体或说二者之一是指向本体的。我认为,所指、能指都不指向本体,其指向认识。
显然,多数人对艺术本体、本体论的维护不是出于理性,而是出于情绪。人们在反对阐释、学术建构时最习惯引用贡布里希在《艺术发展史》引言中的一句话,“现实中根本没有艺术这种东西,只有艺术家而已”。然而,我们可以用孟德斯鸠和爱弥儿·涂尔干的话来反对贡布里希的这种谬论。孟德斯鸠说过,“社会诞生时是共和国的首领在创设制度,此后便是由制度来塑造共和国的首领了”;涂尔干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与行动有所关联的思维创造了实在本身”。可以看出,贡布里希并没有考虑到一点:在漫长的人类文明演进进程中,艺术本身已经附着上了太多的文化印记,问题只是人类习惯认为艺术是由艺术家缔造而已。这类似于人类与文化的关系——文化起初是人类的创造物,但当文化形成体制后,它变相创造了人类。因此,统一的本质主义思想之于当前文化、艺术的认识局限性太大。事实上格林伯格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感知到了这一点。他在《前卫与庸俗》一文中就已提到,光有美学内部的研究在他那个时代回答有些问题已经远远不够,“有必要比以往更紧密、更具原创性地研究特殊而非一般个体所遭遇的审美经验与这种审美经验得以发生的社会和历史语境之间的关系”。或许,我们时代和我们时代的文化也面临着相似的难题。而解决审美经验与文化、社会相关的问题,社会科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以及相应的自然科学已经显露出绝对的优势,“批评性艺术”恰好显现了这其中某些学科的优势。或许,人们不应该依据自己所见到的,而是应该依据自己所预见到的来做判断。(原载于《画刊》,200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