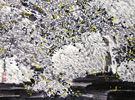图像转向与语言转向
单纯地把视觉与后现代对应起来,即“后现代主义即视觉文化” [xxiii]这种观点是经不起一驳的,因为它只是巴拉兹视觉本质主义的某种当代回声,它抽象出所谓的视觉性,并把它归因到某种文化形态的根基上。这种视觉本质主义的一个特征,用米克·巴尔的话说,“就是喜欢哀悼一直以来被认为居于统治地位的语言帝国主义的衰落”[xxiv],即它总是把视觉与语言对立起来,并宣称建立在视觉性上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已经在击败了以语言模式为政体的现代主义文化之后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很多视觉文化研究学者热衷于谈论视觉在当今文化中的主导地位,而很少反思那种占据了主导地位的视觉是什么样的视觉,在巴拉兹那里作为文化理想的内容,到了他们这里似乎已经成为了现实的实然状况。在本文看来,当代文化的视觉化根本上由消费文化、媒体文化所推动的文化编码的视觉化,视觉变成了一种话语符号,甚至一种连符号也不是的拟像躯壳——视觉这里虽不是一种表征,但也不是一种重新出场——巴拉兹理想中的“可见的人”是一种生机勃勃的、英雄主义的主体,而在拟像的世界中,主体已经消亡了,虽然人们每天都在接触大量的“视觉文化”。
谈论这样一种“视觉文化”,必然要与诉求一种以视觉性为名义的异质的合法权利相区别,前者的经验研究与后者的批判策略根本不是在同一个讲台上发言。在后者那里,只有同质性与异质性在结构意义上的对立,而根本不存在语言与视觉的对立,如果说有一种“视觉性”的话,那么它只是差异性、不透明性、不可通约性,不可解读性等诸多异质性的代名词,而不是对所谓“视觉文化”的基础主义的归纳。在这个意义上,是不可能有一种建立在视觉性上的视觉文化的,因为这种视觉性本身就是反对文化同一性的,如果我们把文化理解为一个既定的表征系统,那么视觉性或异质性恰恰是要反对这种表征系统,而当它被吸纳入这个系统之后,它就已经是话语的一部份了。
说到底,谈论视觉性是为了谈论异质性,实际上,视觉文化研究本身就是人文学科中的一个异质因素,它反对将自身纳入一种学科规划中,即它反对为自身抽象、划定出一个研究对象。而米尔佐夫却把它所理解的“视觉文化”当成了视觉文化研究的对象,又把所谓“视觉文化”的归因到“视觉性”上,再把“视觉性”与“语言性”对立起来,以证明他所理解的“视觉转向”已经发生了——这已经远离了视觉文化研究的初衷与真正价值。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视觉在这个图像时代的主导地位,但它主要是作为消费、媒体文化的并发症状,这种“视觉文化”应该是任何一种以维护异质性的权利为出发点的理论的反思的对象,何况我们不能把这种并发症独立出来,而必须在一种病理学的视野中回溯到它的根源。
如果我们把后现代理解为一种由消费、媒体文化带来的社会整体文化状况的话,那么勉强可以认为,视觉表征的繁荣,以及相随的语言表征的衰落,是这种后现代文化的症状之一(但远远不是全部),这只是一种症状,而不是病根。在这里,还是要再次强调这样一种根本的差异:作为理论话语的后现代主义并不是作为文化状况的后现代主义,或者说,法国思想中以利奥塔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理论话语,远远不同于美国学院中以詹明信为代表的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前者旨在颠覆既定的文化制度,而后者所做的只是在描述既存的文化事实,然而,像后者那样为目前的文化状况加上一个“后现代”名头的意义何在呢?这只是一种学院内部的理论生产而已,并且,我们能看到米尔佐夫在这种理论生产中用视觉与语言的对立不自觉地在为既定的文化制度寻找着合理性,这就是他把视觉与语言的关系提升到本质对立的层面上来所实际达到的理论效果。
与米尔佐夫相比,米歇尔的“图像转向”则要谨慎,也要有价值些。虽然米歇尔也做出了公共文化领域已经发生了一场“图像转向”这样一种表层的文化判断,但米歇尔的重点却在于提出一种学科领域内的号召:把图像表征模式纳入到学科研究的视野中,其意义的可能基础在于:
观看行为(spectatorship)(观看、注视、浏览,以及观察、监视与视觉快感的实践)可能与阅读的诸种形式(解密、解码、阐释等)是同等深奥的问题,而基于文本性的模式恐怕难以充分阐释视觉经验或“视觉识读能力”。[xxv]
在米歇尔这里,观看与阅读,或者说视觉图像与语言文本之间并没有本质层面上对立,他只是在表征模式的框架内思考图像表征相对于语言表征的差异性,并强调人文学科要去重视这种差异性。虽然对图像表征与语言表征之间区别的思考从皮尔斯那里就开始了,但是一直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主流的符号学理论一直建立在索绪尔的语言符号理论上,以语言模式为典型的符号模式,并把这一模式推衍到其他的符号上,这导致了人们把任何图像包括绘画都视为是一种语言。在密歇尔看来,这就是语言学转向带来的不尽人意的结局,因此他提出应该有一种“对图像的一种后语言学、后符号学的再发现”[xxvi],并把这一倡议命名为“图像转向”。
就其内容而言,米歇尔的这一观点是值得深入下去的,但就其提出的语境而言,它却是建立在一系列的误解之上的。实际上,那种以语言模式应付图像的方法,与其说是语言学转向的后果,还不如说是符号学片面性的误区。米歇尔误解了语言学转向的要旨,罗蒂归纳的“语言学转向”是指哲学把语言作为其思考的核心,而不是把世界理解为一个文本,哲学在其语言学转向中恰恰在批判那种语言对应于世界的观念。
在语言学中,索绪尔把语言从对世界的依附中独立出来,揭示了语言乃是一个自足系统的实质,从此,语言不再被视为一种客体的对应物。在分析哲学那里,虽然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哲学渴望着建立一种图画般的逻辑语言,在这种语言中:“一个名字代表一件事物,另一个名字代表另一件事物,并且它们是相互联系的,整个地就像一幅生动的图画一样地描画出原子事实来。”[xxvii]然而,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却意识到了这样一种逻辑性的命题语言在日常语言的“游戏”中是不存在的,语言不可能如此符合逻辑地对应于世界,因此,他抛弃了那种语言图画论,“把词从形而上学的使用带回到日常的使用上来”。[xxviii]在这里要提醒的是,维特根斯坦所抛弃的那种图画般的语言并不是米歇尔的作为表征的图像,实际上,《哲学研究》的一个特色就是把大量的图形及图像纳入了思考中,但不再是标记-客体-概念的语义学思考,而是标记/语境/概念的语用学思路。在罗蒂那里,拒绝语言对应于世界的观点则更加强化:“必须把言语不只理解作并未外化内部表象,而且理解作根本不是表象。”[xxix]在这个意义上,罗蒂才说“我们应当把视觉的、尤其是映现的隐喻,完全从我们的言语中排除”[xxx],也就是说,罗蒂要排除的并不是图像的表征,而是对语言作为图像化的理解。然而正是在这里,米歇尔断章取义了,他把罗蒂的这一观点理解成“语言哲学对视觉表征的总体焦虑”。[xxxi]
语言哲学忽视了对图像表征的研究是一个事实,但这并不是出于语言的自大,而是出于对图像表征的特殊性的尊重,图像作为符号有着与客体的相似或直接的联系,所以它能够不借助于概念而与客体直接发生关联,因此它与语言有着一定的区别,所以图像一直未被纳入到语言学哲学的主要视野中来。在这个意义上,米歇尔提出图像转向是有价值的,确实,我们需要全面完成语言学转向中尚未完成的部分。在这里,我们视图像转向为语言学转向的(应该发生的)一部分,其理由是,语言学转向的发生是从认识论,即那种心—物结构的思考转到对作为心—物中介物的表征符号的思考上来,正因为这种转变,能指的存在才被意识到,因此图像作为一种不应被忽视的表征符号的问题必然要被提出,而其相对于语言表征符号的特殊性也必然要被注意到。但这种特殊性决不能夸大,图像符号与客体之间被认为的相似性并不是先验的,而是一种文化表征实践的结果,即图像与客体之间的相似性的成立依赖于一个“再认共同体”,布列逊对再现性图像的分析已经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xxxii]而古德曼对“相似性”的研究更是指出了相似性依赖于解释,甚至“它就意味着解释”。[xxxiii]
无视图像与语言之间的区别,或者拿语言模式覆盖一切表征模式,并不是语言学转向所带来的,而是把应用符号学片面地建立在语言符号学的基础上的结果。实际上,在符号学的内部,也有着诸多观念及方法论的分歧,语言模式从来没有一统天下过,米歇尔的“图像转向”也可以被理解为符号学内部不同观点中的一种。因此,“图像转向”的提出有其意义,但却不应被估计得过高。
而如果我们考虑到语言学转向内部的从语义学到语用学的转向的话,那么相比之下,“图像转向”的提出就显得保守而滞后了。语用学转向使人们不再停留于对符号意义、概念的探究上,而进入了对其意义背景,即语境的考察。当然,米歇尔无法忽视这一点,因此他强调了图像转向是要把图像“当作视觉性、机器、体制、话语、身体和图形性(figurality)之间的一种复杂的相互作用”[xxxiv],但显然他依然没有抛弃那种对视觉性、图形性的本质主义理解,因为他在把视觉性、图形性不加反思地与图像这一实体联系起来。这种思维再往前一步就是那种“当代社会的文化就是视觉文化”的庸俗断言,它急于宣告视觉已经取得了统治地位,而语言则被废黜到了边缘,因此“图像时代”在这种错误思路中成为了对这个时代的一种断言。
但本文却只是把“图像时代”视为关于这个时代的一个议题,在这一议题中我们触及到了这样一种状况:这个时代的视觉要么是一种语言模式下的表征符号,要么是一种丧失了意志力的,即与体验无关的视觉,总之,那种作为左派理想的与异质性相关的视觉在这个所谓的图像时代恰恰是缺席的。同时,我们也触及到了这一点:种种把“图像时代”作为一种断言的话语都是在为视觉化的规训方式所带来的贫乏提供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