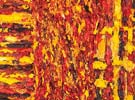1970年代,栅格主题得到肖恩·斯库利(Sean Scully)进一步诠释。他使用不同颜色、纵横交错的线条来构建画面。作品含义与灵魂观念相关。1980年代早期,他开始解构栅格,他的画面只留下几根宽大线条,几何图形穿插其中;颜料使用偏向柔和、相近却不重叠的色彩。此后10年,在后现代的抽象艺术家作品中,栅格以不同方式再次重现,其中彼得·哈雷(Peter Halley)和乔纳森·拉斯克(Jonathan Lasker)表现突出。不同于60年代极简主义,也不同于70年代的多拉兹奥(Dorazio)和斯库利(Scully),这些艺术家将栅格从以往几十年的严谨形式中解放出来。事实上,这些在80年代初涌现出的抽象艺术家采用描绘具象作品的相同逻辑来处理抽象主题。他们观察社会结构、观察景物、对市场营销作意识形态的症状分析,这些观察成为绘画参考物。与其说艺术家是在栅格上创作,不如说他们形而上学地重新发明了栅格的含义。采取相同的姿态,丁乙把注意力集中于对大都市生活的观察。在这些象征现代性的都市中,真实与幻觉的界限逐渐隐退。他记录嘈杂,拥挤的人群,股市指数图表、还有摩天大楼,以及将大都市变成壮观秀场的人造光。这些观察激发他画出带有荧光色泽、金属光亮、耀眼的,色彩斑斓的画作。在一些作品中,他的栅格的震撼效果使人联想到无数的发光二极管,迅疾的信息在其中展开,也让人联想到超大屏幕,其中放大的图像将形成图像的像素一览无余,甚至使人联想到放大的四色图像的印刷品,其中灰网的图像被置于前景,将原初的具象变成了当代抽象绘画。
创作于1988年,使用十字符号的首批画作中,丁乙只使用三种颜色:红色、黄色和蓝色。在四色凸版印刷品中,三种颜色的重叠,随着黑色的加入,足以展现整个光谱,忠实再现图像。当然,印刷的涉及并非偶然。丁乙本人曾明确指出他对十字的兴趣来源于观察:符号“+”是印刷中定位四色的方法。十字是一种在实际操作中最适合确定图像焦距的图形记号。因此,根据符号“+”的实用意义,丁乙逐步将十字转换成一种基本形状,并用不同方法对此形状进行缩小、放大和分层。同时,为避免手绘失控的风险,他意识到需要放缓绘画速递,需要设置障碍抵御自动化作画的风险。为了约束这种被他本人称为“直接书写的乐趣”,1997年他开始使用苏格兰布作画。因为有着确定的形式结构,这些印有格子图形的织物造成了一种限制,丁乙必须从既定形式开始,克服限制来找到自己的风格。在此意义上,绑定在画框内的格子布完全不同于现成品对于杜尚(Duchamp)的意义,杜尚使用日常用品只是为了改变其含义,不改变其形式。展示颠倒的小便池以倒转液体流向,并称其为《喷泉》(1915年),这不妨碍我们辨认小便池。与其说要震撼我们的视觉,杜尚更希望刺激我们的思想意识。为了强调现成物无关紧要,他解释说他选择物品只是因为它们的平常。他甚至走得更远,将他的这种方式称为“冷漠的美学”。丁乙使用的布料也属于大众消费的工业产品,但他把他的栅格重叠其上,他抹去其下的印刷记忆,印证这点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他最终目的是构造一种图像,这种图像在形式层面上对应于现代大都市的混乱状态。
将城市作为他的参照物,丁乙随着莫里斯·郁特里罗(Maurice Utrillo)及保罗·塞尚(Paul Cézanne)的作品开始他的观察。郁特里罗描绘他那个时代、蕴含着新时代的精神的巴黎,就如同上海蕴含着当今时代精神。就塞尚来说,他叠加非常细小的点彩来营造整体效果。他的绘画基于这样一种前提:光感产生于我们的视觉器官,我们由此根据高光、中间色调与四分之一色调来区分各种平面。在构造画面时,他从一个色点开始,在这个色点上再叠加其他色点,次数增加,色点越来越大,直到形成可以辨认的形式。
丁乙使用一种近似于塞尚的构造逻辑,他层层叠加十字,通过确定不同的透视点和视觉面,最终使画面达到形式平衡。塞尚描绘平静的乡村风景,而丁乙描绘大都市景观的视觉喧嚣。这份喧嚣使得他的作品和那些在1960年代尝试过栅格主题的抽象艺术家的作品之间有了意味深长的区别,使得他的作品成为一种象征,表示拒绝再现任何形式的实际景物和情感。
在讨论那个时期的艺术时,罗塞林德·克劳斯(Rosalind Krauss)认为,挪用栅格主题的现代艺术家将重复等同于虚假和抄袭。既然只能被不断重复,栅格就要求艺术家固执地一次又一次地复制相同的形式结构,有意识地摒弃在形状演变过程中追求创新的念头。克劳斯的结论是,栅格使作品不受叙事性侵入的能力使得作品保持着客体一般的的静默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此前也谈论过现代艺术作品中的静默问题。在1967年的一篇文章中,桑塔格指出,当代艺术家对静默的兴趣和他们对所有无法用言语和图像说明的东西的兴趣是一致的 。从史学角度说,她认为,艺术品产生的静默应该被认为是作品本身“绝对性”的结果。“绝对的艺术”就是作品从现实环境中脱身而出,桑塔格这么说,也就在含蓄地指出持久存在的艺术的悲剧性。克劳斯的论点与十多年前桑塔格发展出的一个观点相同:关注语言的活力,赋予主体相对的重要性。但当今艺术已脱离开这些设定,就像丁乙的作品,他给予对象只是一种相对的重要性,不认为作品只是符号的自我指涉系统。毕竟,丁乙的艺术风格形成于1980年代,在那个历史时期,因为远程通讯技术的变革和全球化运动,社会已变得抽象。因为身处这个转折点,人们由个体转变成消费者,大城市变成大剧场,大剧场需要将景观变成一种表演,从而忽视那些生活其间的人的需求。凭借其土生土长于上海的优势,丁乙目睹了这个划时代的变革。上海,在近几十年间,通过由摩天大楼和硕大建筑组成的新的后现代大都市景观,重新定义了它的身份。这种变化的活力反映在他的作品中,作品是抽象的,没有历史性和文学性的叙述,只是将他周围的形态和符号做一种概括。
当然,艺术作品无法回避表达作者的内心世界,这个内心世界包含着与经历有关的记忆和情感,也包括对地域的记忆。丁乙面对的挑战之一就是要保护与他记忆有关的价值免遭现代主义语言和全球化世界中文化同质化的冲击。自1988年用交错的线条创作了他的第一幅作品开始,他运动于多条战线:为了表达纯形式,必须去除十字的实际和象征的意义;摆脱现代主义的影响,以解救自己的艺术;他重构他称自己称之为“停滞的传统文化”的踪迹(特别表现在那些用粉笔、木炭、彩色铅笔和圆珠笔绘成的作品中),将其比喻为“埋于地下,被风雨侵蚀”的历史古迹。表面上看,这些目标似乎相互矛盾,因为二十世纪先锋派的宗旨之一就是将符号带回零度状态,并认为符号本身就有足够的意义,他们不断尝试清空作品中的历史记忆。丁乙依靠栅格,巧妙地超越了这些矛盾,我们将会看到,栅格是个属于过去、暗示当下、设计未来的主题。我们发现这样的栅格结构存在于古代木建筑中、存在于人类首次出现的装饰中、存在于公元前五世纪希波丹姆式的(Hippodamus)城市规划中,存在于门和窗的格栅中,如此等等。在简·尼古拉斯·杜兰德(Jean Nicolas Durand)(1760-1834)的建筑中,栅格概念代替了中心透视的概念。正是通过再次使用栅格,立体主义得以重新定义图像性质,造就了一种没有中心透视的形式。下水道的阴井盖上、在编织物和纺织品设计中、在现代楼宇的立面上,我们可以找到栅格;在电脑芯片的编排中,我们也可辨认出它的形象。正如我们所见,在象征、形式和时间层面上,这些不同形状的栅格很少相同。它们之间的差异如同建造古代房屋结构的十字木料和摩天大楼立面之间的差异,如同古代装饰和电脑芯片编排方式之间的差异,如同中世纪阿拉伯风格的凸肚窗和蒙德里安交叉线条系统之间的差异,如同蒙德里安作品和斯库利作品之间的差异。如此等等,直到我们看到的丁乙的作品。正如蒙德里安和马列维奇(Malevič)超越以往艺术对栅格的形式使用,丁乙同样超越了现代西方艺术家对栅格的形式使用。这是因为,栅格这个主题本质上是开放的,在形式上和理论上,它的发展无法预知。
德梅特里奥·帕帕罗尼Demetrio Paparoni
翻译:邬晨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