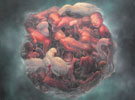劳:同样你不需要被归入“这是一幅绘画”、“这是一个雕塑”的分类法。这种分类在这儿不存在。这是最大的不同。如今这也被归入一种门类了因为它在那儿。而后就有了大量的关于什么可以被归入这个门类的争论,这时候我就走人了。这太没劲了。
玛:之后就是这样,“这是身体艺术。那是身体艺术。”在20世纪80年代市场要卖东西。身体艺术不是能卖的东西。这一运动就停止了,你也随着这运动死了。这真的很重要——你如何活下来。约瑟夫·博伊斯()一直与激浪派(Fluxus)和偶发艺术(Happening)相联系,而当后两者死去时,博伊斯活了下来。这也是发生在你我身上的事。我们从这类艺术中活了下来。我们开始成为我们自己,独立工作,不带着任何运动的标签。我想问问你——当你与华纳兄弟公司(Warner Brothers)签约时(在1981年个人专辑《噢超人(O Superman)》在英国流行歌曲排行榜位居第二位之后),这确实是你一生中不可思议的一刻。你是那个时期唯一从艺术潮流进入主流的艺术家。
劳:我听到很多这样的屁话:“你正在热卖!”两年后他们会问“我怎么卖?”事情是这样,我录制了500张唱片,400或500美元一张,我在家里提供邮购。人们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地址。我记下来,将唱片打包,而后我去运河街邮局将它寄给某个人。所以而后有一天我接到一个来自伦敦的电话:“我们想订购一些唱片。”我说:“好啊,多少张?”他们说:“这周五要4万张,之后周一再要4万张。”我说:“啥?!好嘛,我马上回给你。”我给凯伦·伯格(Karen Berg)打了电话。她任职于华纳,有一回她来看我的表演并说:“我想请你制作唱片,我想请你为华纳兄弟公司制作唱片,”我说:“我不想做唱片,我是艺术家,不是流行歌手。”无论如何,我给她打了电话,说:“你能帮我吗?我需要相当快速地制作一些唱片。”而她说:“我们在华纳兄弟唱片公司不是这么做事的。这儿有一份合同,8张唱片。”我像个人类学家一样处理这件事。因为突然进入一辆车又走出一辆车,100个人喊叫着你的名字——这只是很荒唐。我想“这蠢到家了。”而你知道你将会穿越这些。所以我享受它而不依赖它。
玛:谈谈这种跨界吧,我出现在《欲望都市(Sex and the City)》中(在第86集中,一位艺术家表演她在画廊中不进食不喝水,像在玛丽娜的作品《海景房(The House with the Ocean View)》中一样)——你看了吗?
劳:没看。
玛:那是在印度,肖恩(Sean)(凯利[Kelly],画廊主) 给我打电话说:“他们想让你出现在《欲望都市》剧集中。”我那时完全不知道什么是《欲望都市》。我说我不想做,但如果他们想用(我的)作品,他们要向我买版权。所以他们付了我版权费。他们扮演我的样子很滑稽,像个巫婆一样坐在那儿,眼睛下面是黑的,而后巴瑞辛尼科夫(Baryshnikov)来保护我。真差到家了。但这是第一次有个从未和我说过话和打过招呼的、在街角卖菜的女人开始对我说:“啊,你想要点儿草莓吗?它们很新鲜。你不用付钱,拿去吧。我真的感受到大众的力量意味着什么了。”很神奇。免费的草莓,而还有招呼。这很小规模地(与你的名声)相比较,因为当你创作“超人”时,它红极一时。确实是跨界,某种程度上你真的跨界了,而后你又回来。而这经验是不同的。达明·赫斯特(Damien Hirst)是跨界的一个好例子,尤其是他的钻石骷髅——艺术作品的浮华,正是它所意指的。那是一个很棒的例子,以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代表了我们做过的事。它确实是一件伟大的作品。某种程度上它跳到了另一面。对劳丽来说,这不是什么努力。对赫斯特来说,他付出全部努力进入大众文化,靠金钱,靠投资,靠整套机制,靠与我一直以来的研究全然不同的经历,并靠220名助手。杰夫·昆斯(Jeff Koons)才有86名助手!我只有一名。满打满算也只有一名。我至少还需要一名,但就这样了。关于你的机构怎样从一个人发展为这样巨大的制造厂的想法。你拥有它。你必须提供工作,而后你必须生产。而后你过度生产。而后你问自己:“艺术的意义将走向哪里?”
劳:我记得(美国画家、雕塑家)埃里克·费舍尔(Eric Fischl)曾说:“我不觉得我是艺术界的一部分,我只是艺术市场的一部分。”我想:“我确实要制作唱片,因为它们很便宜,这样我花20美元就能做演出,而且我也用不着去见那些藏家之流,他们让我发疯。”
玛:我曾经去看过一次拍卖。太雷人了。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的作品比好多你甚至都记不住名字的人的作品便宜那么多。
劳:那只是成了另一种货币。某种惹人迷醉的东西。但当你去到那些大的博览会,而后你开始推销你自己。这就是我一年来对自己保证不让自己的照片参与其中的原因之一,因为我无法忍受这个。不让我的照片出现在里面使我感到如此解脱。然而我愿意参与我关注的事。照片可以放在那里,我喜欢关于人的照片。并不是我有什么反对这个的想法。只是对我个人而言,我有时想:“让我退出一段时间。”你准备好(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展览)了吗?
玛:还没有呢。我有很多担心的事,劳丽。我真的很怕。
劳:你怕什么呢?
玛:我很担心,有千千万万的状况可能发生:比如我生病,比如我的后背疼痛难忍,比如我憋不住尿——所有这类状况。唯一能与之相提并论的是在中国三个月徒步长城。但这是比较特殊的一类情况。去长城徒步就是为了见面、也为了说再见。在情感上很难,身体上也很难。而后就是这次。每个大任务都是净化的一部分。这是部分个人原因。接下来就是一个大任务。我确实感到我几乎担负着历史责任,将行为艺术带到那座博物馆中,而后后来人得以真正理解主流艺术中的行为艺术。我同样担心所有那6名表演者。
劳:都有谁?
玛:不同的人,有些青年行为艺术家和舞蹈家。非常不同,舞蹈家的身体与行为艺术家的身体之间的差别。舞蹈家的身体是经过训练的身体。行为艺术家的身体是未经训练的身体,然而他们有毅力。
劳:你有没有成立一个“玛丽娜训练营”?
玛:(笑)就是这回事。我带他们到乡下——禁食,一段时间,在冷水中游泳,全睡在谷仓中——在9月初建立这个团体,来看看优势在哪里,我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你改变一下想法没问题。然而我谈的是6个人同时改变(他们的)想法,所以他们真的必须有耐力、奉献精神和健康的心理素质才能在那里待上3个月。任何事都可能发生。这是我们必须探索的未知领域。
劳:你真的必须对人们进行心理训练。
玛:我们准备重做的作品是在博洛尼亚(Bologna)的博物馆进门的那个(在1977年的作品《无量之物(Imponderabilia)》中,阿布拉莫维奇与其搭档乌雷(Ulay)裸身站在市立现代艺术馆(Galleria Comunale d'Arte Moderna)门内,进入参观的人们必须蹭过他们的身体才能走进去)。我们邀请4对夫妇做这个作品。每对夫妇做两个半小时,像保安一样,他们穿着外套进来,脱下外套站在那儿。之后下两位进来脱下他们的外套,(之前那两位)就回去。这个作品不简单。参观者那么多。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除去紧贴着这样的问题之外,参观者还会踩着你的脚进去。(笑)但你瞧,这是一件你做过三小时就这辈子都打死不做了的事,而做三个月又是另一码事了。我们正面对难以置信的单纯的实际问题。
劳:但这次你有了你自己的“军团”,这很棒不是吗?你以前从未有过。
玛:是啊,从未有过。这是另一件有趣的事。同时——我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古根汉姆博物馆(Guggenheim)将整座博物馆都交给蒂诺·赛格尔(Tino Sehgal)进行1月份的行为表演。正好在我的表演之前。这次将有400人参加表演。他的作品将以非常年少的人作为开始,随着那螺旋上升,将有年纪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的人,只是站在那儿。这确实棒极了。几年前这是无法想象的。我一直相信经济危机和行为艺术是有联系的:经济危机越严重,行为艺术就越繁荣。这是一种反作用。劳丽:每次我看见经济一下滑,艺术就更好一点儿,不管是绘画还是音乐还是别的什么。所有人突然都必须得走了,“我下一幅要在我的车库里面画了,”然后上面会溅上一些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