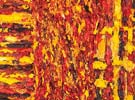文人大写意能不能代表中国画的全部
如果说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画的格局是以明清大写意与元代小写意、唐宋严谨画风的先后兴盛而呈三足鼎立,那么1980年代的学术界,最初是将文人大写意视作为中国画的杰出代表。郎绍君“二十世纪传统四大家”观点的提出,是这一转变最具代表性的体现。
郎氏肯定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这四家的成就,诚然准确,并且他提出近现代画史上中西合璧派与传统派的并存,立论精当,其说影响广泛因而顺理成章。然而,他认为上述四家代表了整个二十世纪传统中国画的成就,其实并不全面。严格地说,这四家应定义为“传统金石写意”四大家,否则,非但漠视了以张大千等为代表的另一支取法唐宋的重要的传统力量,而且对以傅抱石等为代表的红色经典亦有回避之嫌。这一观点,或许是作者对建国后中国画刻意强调主题创作抱有不同见解,而且与1950年代以来大陆国画界潜在的思维定势颇为相关。
需要说明的是,独尊文人写意画的思潮在进入新世纪后同样遭遇了物极必反,徐建融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与郎绍君等相左的意见,鼓吹以工致深入见长的宋元画风,并激烈地批评明清文人写意画。徐的观点亦引起了很大争议,然而指出文人大写意不能代表中国画的全部,却是其说的价值所在。
矫枉过正、物极必反的另一大表现,乃是李小山“中国画穷途末路”说的提出。其立论根据是中国画,尤其是文人画乃封建社会产物,在社会结构已发生巨大变化的当代,必然失去发展空间。缘此,一些学者也推导出中国画必须通融西方现代艺术而进入“现代”的理论,一时间此种学说开始广为人们接受。
李的观点,对打破极“左”思想禁锢与接受西方现代艺术,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其致命的问题,是延用了长期盛行的简单化的阶级斗争方法,也即前述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的教条化理解。依此类推,非但中国诗画、戏剧等所谓“四旧”,而且中国传统工艺如筷子、食品,都恐因其“封建性”而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准此,中国画也势必被西方现代艺术所取代,传统艺术只剩下为西方文艺增添地域性文化元素的价值(此种隐患目前仍广泛地存在于包括当代绘画、影视在内的文艺界)。这一观念,事实上与江丰当年从世界性的角度主张以油画取代中国画,出于同一逻辑。“左”的思想多年的影响,已造成人们的日用而不知,当时有学者提出潘天寿是“没有跨入现代的最后一位大师”之说,同样也属此种观念的延伸。中国画的“现代”之说,是在振奋人心的1980年代提出,但却不可避免地沾溉了此前理想化、“大跃进”式的“赶英超美”习气。
矫枉过正、物极必反的又一大表现乃是吴冠中倡导“形式美”,此说是对建国后文艺界唯“形式服务于内容”的定律是从,美术界定写实于一尊的物极必反。在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整个绘画界掀起了崇尚形式表现与抽象审美的热潮,声势至今浩大。事实上真正奠定吴冠中学术地位的,正是他对形式主义审美的倡导与实践,而非是其成名后被热炒的“笔墨等于零”。1990年代,卢辅圣在上海书画出版社组织董其昌、四王、赵孟頫\等一系列国际学术研讨会,从笔墨形式的角度重新认识古人,影响巨大。这既是对当年武断批判文人画的反拨,也令董其昌、四王、赵孟頫\的绘画,自此不再成为罪恶,同时也恰恰是形式主义美学渗透入中国画史论研究的表现。
至于吴冠中的“笔墨等于零”,其实只是西画出身的他对自己宣纸彩墨画创作缺乏笔墨修为的一种曲意辩护,在学术上并无价值,当然对新闻媒体,这又当别论。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两种不同笔墨系统”的学说,从某种意义上也可视作吴氏申辩的学术化表述。其说的核心,与一度兴起的“现代水墨”在观念上甚近,即认为只要用水墨、宣纸,而无论是否学过中国画,画出的同样是笔墨。此说只承认笔墨的表相,而否认笔墨的内涵,实质是认为“非笔墨”也是“笔墨”的一种。然而依此类推,中国民间自古有用油漆描绘、装饰器物的传统,国人是否因此能与欧洲人同享油画的发明权?绘画的笔墨,实际上只能是指传统中国画的笔墨,舍此再无其他。概念有内涵、外延之分,以外延混淆内涵,或者说“白马非马”,固是智慧,但毕竟多被用作辩术。在现实中,我们不会因为人与鸡都长毛,就承认人等于鸡,或者将“不是人”当作“人”的一种。当然“现代水墨”的主张并非是为吴冠中辩护,而是旨在借水墨画的民族特色,为中国现代艺术谋取其于国际主流艺术圈的一席之地。因而此种学说,非但同样带有鲜明的“大跃进”色彩,而且更脱离了艺术范畴而成为一种政治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