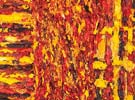三、中国抽象艺术的当代表述与本土化路径
今天,“发现东方”成为了知识分子的重要任务。因为中国不可能被他者发现,我们只能在全球化和后殖民语境中,自己发掘出文化的新精神和新生命,才能厘清中国的问题,找到适合自己的中国道路。“一方面是中国在认识与更新世界中认识与转化自己,同时在更新自己中更新世界;另一方面则是中国的内涵的生成必须在它自身的古今视野的融合中实现。这两个方面共同塑造了百年中国的基本问题意识,这就是所谓的古今中西之争。”[20]这即是高名潞先生说的“现代性是实践的、历史的、发展的,不同地区的现代性不同。”“现代性就是一种时间和空间的错位。”[21]中国抽象艺术如果不注重在地性、区域性、文化特殊性就会掉入新的霸权主义之中,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这个机械复制的年代,中国抽象艺术必须以自身的存在去自我呈现,避免对所谓中国化抽象的表象解放而压抑了中国抽象艺术家的自我演变能力,从而无法拓展自我的生长空间。
从当代艺术史看,较早提出抽象艺术本土化的艺术家应该是吴冠中,在改革开放时期就强调他的抽象绘画离不开传统,所谓“风筝不断线”,积极摸索抽象艺术的形式上的本土化,其路径主要是主要是学习西方的形式之美又回归中国传统母体。但由于只是对传统的表面化理解,而缺乏语言的真正内涵,其价值取向更多地体现在对主流艺术的意识形态的反抗上。后来的艺术家葛鹏仁、孟禄丁、尹齐、周长江、王怀庆等艺术家虽还是以借鉴西方抽象艺术为主,但他们的作品呈现出更多的本土意象文化与思维的特质,在抽象语言方面的探索也为后来者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导引。更具有个人话语意义的抽象艺术家于振立、王易罡、马路、管策、江海、祁海平、张国龙、杨述、曲丰国等以及这一时期许多抽象水墨的实验艺术家的作品,都可以说日渐走出了85新潮的社会文化批判理想,脱离了非本质的抽象艺术模式,越来越注重个人体验,注重个人对现实非理想状态的真实感受与态度,追求艺术语言上的可能形式和本质性探索,显示出不可忽视的本土性抽象艺术发展态势。当然,不能否认的是,这一时期的抽象艺术在努力构建的过程中,其话语方式从移植、挪用到符号化,都存在着被西方同化的变异过程,并处于西方抽象传统审美标准判断阙如的境况下,逐渐屈从于商业化的惟一尺度,从而背离了历史先锋派精神的自主性和批判性。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与中国抽象艺术的本体语言的有力实践与本土经验的初始探索没有获得有力的理论的支撑有关,也与当时的政治功利思想和空洞的理想主义现实有关。
到上世纪90年代,高名潞开始用“中国极多主义”描述酷似欧美现代意义上的抽象艺术作品。如艺术家丁乙的《十字系列》、张羽的《指印》、李华生反复书写的“格子性”抽象,孟禄丁的《元速》系列。这类作品大多具有较强的思辨性,其存在也并不是自为的,其意义的显现往往需要求助于哲学化的阐释。极多主义强调创作的方法论,要求艺术家在进行创作实践时,所采用的表现方式不仅要有一种独立的、系统的批评理论作为支撑,而且在形式、风格的表现上能体现出一种原创性的价值。高名潞认为这些作品在创作时主旨并非要形成绘画的形式,而是强调绘画的行动过程转化成无止境的观念,既超越了作品客体本身,表现在个人的特定生活情镜中的特定感受及每天持续发展的过程,它的意义并不体现在形式本身,相反以创作的过程性、时间性来彰显其独特的意义。并认为,“极多主义”不是一种抽象风格,而是85时期“理性绘画”在观念和精神上的又一次拓展。无独有偶,栗宪庭也提出 “念珠”与“笔触”的抽象艺术概念,强调繁复的东方美学意味的手工创造过程。与高名潞的“极多主义”有着异曲同工的效果——都试图对90年代以来抽象艺术的新发展做出理论上的梳理。他不是从理论、方法论的维度建构所谓“中国抽象”的“自我”,而只是强调“繁复的手工过程” 。
两位批评家都强调作品的观念性叙事,都认为作品应反对现实的再现,强调创造过程,并用过程的“时间性”来取代作品的意义,都试图用中国的哲学,如“虚无”、“顿悟”、“无限”来对这种创作行为提供理论的支撑。我们知道,“无限”概念在西方语境中主要是与宗教密切相关的,正如列维纳斯把“无限” 归结为“上帝”,但中国哲学语境中的“无限”却没有这种宗教的意蕴,而更多的是对人类生命意义的理解。在《整体与无限》一书中,列维纳斯把“无限”与“超越”等同起来,根据“超越”来理解“无限”的观念。他这样写道:“无限是超越存在作为超越之物的特征;而无限之物则是绝对的他者。超越之物是唯一的思想对象,我们对这个对象只有一个观念;它‘这个对象’被无限地剥离了其观念,外在地看,因为它是无限的。”在列维纳斯那里,“无限”中的“无”意味着一种否定,一种完全的、纯粹的否定,即不包含任何否定对象的否定。由此,列维纳斯特别强调了“无限”概念的被动意义:这样的“无限”是被投向我们的,我们只是被动地接受了“无限”,但我们又是注定要接受“无限”的;进一步地说,正是由于被“无限”所击中,我们的“有限”才有了意义。所以,“无限”又总是在“有限”之中的。[22]岛子指出:“从后现代艺术美学意义上来理解‘方法’,则主要是指从艺术创作实践、艺术批评实践把握现实,从而达到某种目的的途径、手段和方式的总和。正是‘方法’形成了特征,特征使本体可见、可识、可道。尤其后现代艺术本体意义并不凝固在某种统一定律之内,存在的只有变化的意义。我们只能进入具体的艺术现象、艺术批评话语、艺术作品,通过辨证地使用后现代知识不同来源的影响,方可对其变异、游移、缺憾以及建设性的实践付诸探赜索隐的阐释”。[23]
然而,它是否会象萨义德在对东方主义的概念判断时所说的:这种“中国式”抽象的构建会被转化为一种全球化的权力症候,变成实践功能的权力工具,并不懈遏制外部的质疑和反抗呢?抑或如高名潞所认为的,“‘极多主义’必将引向现代禅——中国的达达和解构主义”;还是这种“反形式”的形式创作方式,最终存在着将艺术家创作观念虚无化或无限夸大的危险?我们从其表达过程中所借助的外在视觉形式看,其只是隐喻和象征行为的表面化载体。他们的作品所呈现出的是观念的发生、存在和不断生长的状态,指涉的是艺术家本人对艺术本体以及周遭事物的介入态度。“把行为本身看作一种追求”,将“时间”转换成“空间”的非确定性阐释,而且在空间与时间的表述上没有任何强有力的联系,追溯意念的痕迹及意念之间彼此不断发生的“禅”意,使得其话语显得具有无限的可能性。但“禅的否定不是逻辑意义的否定,禅的肯定也不是逻辑意义的肯定,因为‘本体’不能被人为的思维规范,也不能被‘是’与‘否’的判断形式以及所谓认识论的诸般公式束缚”。[24]或者说,艺术对于生命本身而言,它与禅具备某种必然的联系吗?显然,问题应回到现代性视角,“从康德起,现代性即不再是建立在一个与过去相互比较的问题,而是植根于对自身关系的质问之中。问题的焦点并不是在于何者为新,而是何谓‘当下’,不是对应于深厚悠久的传统,而是相较于完全不透明的‘现在’。所以福柯认为与其将现代性看作是一个历史的阶段,不如视为是一种态度,一种对于当下关系的模式。[25]进一步看,将现实问题化,不仅可以形塑思想的表现方式,更重要的是,它还规范了艺术主体与其所处时代的关系。因为当主体不再是意义的来源之后,即意谓着主体无法再以反思性的姿态独立于世俗与现存的各种决定,也不能再断言可以借由知识去超越历史从外在加诸于自身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