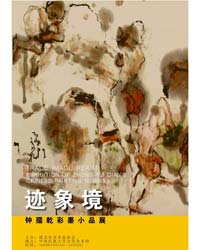问:这段时间摄影艺术史的沉淀,对拐点之后的数码时代的审美观、艺术语言会有影响吗?
蔡萌:我觉得是看需求吧,每个人的方式不一样,当然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悖论,我们在谈数码完全可以不参照摄影,完全可以另辟蹊径。当然,如果说我们现在都在遵循被商人绑架了的摄影摄影概念,去做数码摄影。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既然要认同数码摄影的话,那还是应该把传统的银盐再过一遍,知道它的语言边界之后再去做,可能会更有的放矢,或者是更能够找到一种语言的逻辑,或者是一种上下文的关系。当然我也在谈,数码完全可能是另外一个概念,完全是全新的东西,比如现在有些多媒体的展览,打的那种在墙上一个立面的一个巨大扫描仪,每个人上去扫一下,马上瞬间出现一个影像,或一会儿谁上再扫一下,又出现另一个人,我觉得那才叫数码。我觉得它不需要什么语言,不需要什么法度,不需要任何的一个标准,完全是可以跟大众拉近的这样的一种艺术,这就是当代艺术、后现代艺术的一个最典型的特点,被拉平了,艺术不再变得那么居高临下、高高在上,被膜拜,有一种压迫感。现在是一个艺术变得非常的大众化的时代,变得非常有亲和力,任何人都变得很接近,很容易让人理解,很好懂。
问:中国的当代摄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四月影会”算不算一个开端?
蔡萌:最早是从“四五运动”开始的。因为“四月影会”还是一个跟“四五运动”有关系的群体,所以我更愿意把开端说成是“四五运动”,而且“四五运动”很明显把摄影完全从国家的权利话语迅速变成一个年轻人的个人话语。
问:“四五运动”之前摄影应该算是官方统治的一个工具了。
蔡萌:对,但是“四五运动”、“四月影会”之后其中很多人又进到体制了,又回到一个权利话语的体系了,这当然是另当别论。但是就总体来讲,我所认同的当代摄影应该包括这两个类型,一个纪实的,一个是当代艺术的观念摄影,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四五运动”肯定要放进去了,这种记录的,或者文献的摄影,典型应该放到当代摄影的总体的生态范畴里。但是作为当代艺术的这种所谓的观念摄影,我倒是觉得“四月影会”里头会看到一点点小苗头,它跟“八五新潮”里面出来的,作为当代艺术后来出现的这种摄影,他们之间其实还是有一些隔阂,这两个,它是两个不同的群体。但是他们两个群体里头到底有多少交叉还不好说,会有,比如说85年的时候,“四月影会”里面的林飞就曾经和中央美院的洪浩在一块。
问:中国有没有摄影流派?
蔡萌:要说的话,应该有,比如说三十年代民国时候的画意沙龙摄影,是建立在中国古代文人画基础上的,比如郎静山他们当时在做的那批东西,那应该还算是中国的一个,典型的具有东方独特审美美学标准的摄影,它具备一个流派的一些基本的东西,比如说美学趣味,包括群体的规模,包括参加的展览,甚至获得国际的影响、认可,我觉得甚至它那种影响几乎一直贯穿到现在还在影响。
问: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现了一批行为摄影,像《为无名山增高一米》、张桓的《十二平方》这种照片,从严格意义来说它应该算是观念摄影还是艺术文献?
蔡萌:从两个角度来讲都有可能有这种意义在里面,从文献的角度当然是文献,它是有记录性的,记录了一个行为艺术的过程。要是说从艺术角度来讲,首先它有两种可能性作为艺术,一种是说它有一个很好的摄影家在拍,然后摄影感觉很好,它有一种艺术性。另外就是它的内容本身具有一种艺术性,就是所有人在照片里表演,其实某种程度上摄影就是被拍摄者在照片里表演,拍摄照片的人能够干预和驾驭这张照片的因素毕竟是有限的,所以表演本身是一个非常当代的一种艺术的方式,所以它同样具备了这样艺术的特征。
问:您在《观念摄影在中国》这篇文章当中,提到了中国摄影对西方的一种依赖,是处于迎合西方的一种状态,目前来说对于中国摄影艺术是西方关注大于本土关注吗?
蔡萌:也不能这么谈吧,因为我觉得本土现在对当代摄影这块也挺关注的,可能从某种程度上,比如从市场的角度来讲,西方关注确实大于本土,举最简单的一个例子,中国摄影80%多的藏家和买家都在海外,甚至到90%都是外国人。但是我觉得中国人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更多的年轻人关注这种影像方式,关注这种图像方式,甚至去模仿这种成功的经验,去抄袭和模仿前辈们的这些摄影家,像王庆松,像苍鑫、洪磊、洪浩、黄岩,当他们的图像变成经典之后,就变成了后辈的年轻人学习、模仿、参照的一个对象,被更多的年轻人所关注。在现在高校的摄影教育,甚至是在摄影节上,尤其像平遥摄影节,你会发现貌似这种观念,这种当代艺术的摄影现在是非常的普及,叫现代版的观念摄影吧。今天我们都强调观念,要做摄影的话,上来就说观念最重要,我们都认为观念重要,而这种观念的东西呢,每个人似乎都有,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观点,你也有,我也有,他也有。
问:看起来做观念好像很容易。
蔡萌:对,现在就是说观念变得越来越容易,为什么容易?它背后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今天是每个人都有个性跟自我的一个年代,今天不是文革了,不是人人都被禁锢、被阉割、被束缚的那个年代了。所以我们完全不缺乏那点所谓的什么建立在个性差别基础上的某种观念,或者是某种对艺术的理解的观念。当观念变成借口之后,会发现它变得越来越有点滥情,你说它重要也重要,但是可能某种程度上它又变得不重要了。这个时代的艺术变得越来越有社会性,从杜尚开始强调一种社会性,今天我觉得摄影作为一种记录手段来讲,它跟社会的关系是极其密切的,社会在高速变化的这种前提下,每天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事件,我们又不缺乏这种事件,用摄影来说事儿,用照片去记录事件,特别容易。难在哪儿呢?又不缺个性,又不缺观念,又不缺事儿,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缺语言,语言在我们国内是个事儿,但是在西方可能又不叫事儿。可能是西方的社会太稳定了、太安逸了,没有那么多苦大仇深的艺术家,不像我们,骨子里头都有一种抱着批判社会的态度,往往这种对社会的批判和反讽可能最后都变成一种歌功颂德。今天的艺术真是太复杂了,很难有标准,我觉得还是要回到每个艺术家自己的立场上,是否去真诚地去面对内心,面对艺术,面对自己,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更重要的吧。在某种程度上讲,今天我觉得接触的摄影界的一些年轻人,还是比较值得关注和期待的,因为他们没有那种商业和世俗的铜臭味,还是很真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