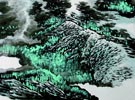僧肇《不真空论》以中道解有无,主不执于有,也不执于无,非有非无,非此非彼,若有若无,若即若离,旨在解除对所有确然性知识的执障,以这样的方法和眼光观察世界人生就叫破执。
汪建伟大概没有使用过这个词,但在他的艺术哲学中却从来不缺乏类似的辩证智慧:
如果我的作品有某种倾向性的东西,我会很警惕。我对暧昧性和不确定性很感兴趣,……不确定本身就是控制,它限制你的作品表现出某种很强的倾向性,(促使你)放弃自恋的、胸有成竹的、自信不疑的、准确无误的思想方式,而将质疑作为工作的起点。
怀疑也许是当代艺术的天性,但汪建伟却常常提醒自己不要使这种天性变成滥情的道德冲动,他宁愿使这种怀疑处于某种中立的状态,以便让观察和对象之间保持足够的灰色地带——这是他最喜欢使用的词汇之一——从而使怀疑成为一种探讨智慧的认知过程,而不是沦为思想的表达或政治立场的陈述,苏姗·桑塔格在谈论当代艺术与思想作为一种新的神话形式时说过这样一句俏皮的话:
艺术本身不是思想,而是从思想内部发展而来的解毒剂。
1历史与政治
在汪建伟的作品中,历史和政治是两个或并置或交叉的主题,但与其说这是两个考订真伪、辨别是非的主题还不如说是两个参悟禅机的“话头”或是“公案”,它希望引导我们走入问题的陷阱而不是事实或真理的终点。
2《屏风》
创作年代:2000年
首演年代:2000年
首演地点:北京七色光儿童剧院
2000年创作的《屏风》是汪建伟第一部真正意义上——就它实际公演过而言——的剧场作品,它的情节线索和叙事结构都有点像卡夫卡的《审判》,虽然它的晦涩和幽默不是克尔恺郭尔式的而是维特根斯坦式的。
故事源于作者对中国艺术史上一个“漏洞”的阅读,五代名画《韩熙载夜宴图》作者顾闳中的双重身份:画家和间谍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历史想象和重读的条件:
“屏风”的过程既是一种对历史与传统的“考古”,也是对我们自身“阅读”历史方法的“考古”,像维特根斯坦所言:“事物对我们最重要的方面由于简单和熟悉而被隐藏起来”,再没有比被“阅读”了近一千年的艺术更让我们熟悉的了,什么东西被隐藏了?
围绕这个假设性疑问虚构的情节像是一团乱麻,“案情”由一群南唐画家谈论“等待中”的审讯开始,审讯谁、谁来审讯和审讯什么都极度的不清晰,甚至:
朱锐:我们不能证明我们是在等候审讯,还是等候问话。
第二幕的人物关系似乎清晰起来,审讯者差役对被审者顾闳中的验身是高度实证性的(28条体征):从身高到视力、从疤痕到皮肤类型、从畸肢到体臭,但接下来的情形又使“历史阅读”变得暧昧起来:
顾:既然像你说的,我被你逮捕了,那我为什么没有被你绑起来,我也没有带上手铐,怎么能证明我是被捕的?
差:我们从来不用那些东西。
顾:那我无法证明我是被捕的。
差:我只负责逮捕,不负责证明你被捕,那是下一个程序。
顾:可是我现在还可以出入房间,看电视,打电话,我还有钥匙,我可以去上班?你像个机器。
差:我也不负责听你的个人想法。另外。你如果坚持你不是顾闳中,你就没有被捕,我们逮捕的是顾闳中。(差役下到屏风后,顾转饰无名氏)(灯光暗场)
就这样,一场有着明确法律关系的审讯暗演成一场滑稽的诡辩,而被告人的“转饰”使接下来的场景变得更加诡异,审讯变成了所有人物的“描述”、“回忆”、“抗辩”和“互证”,伦理、艺术、正义、人格问题的混乱搅拌使对“历史”的阅读和考订毫无希望地演变成为一场语言游戏,它们遵循的不再是历史的逻辑而是维特根斯坦揭示的那个“遵守规则”的悖论:如果任何行动路线都可以自行解释为符合规则,那么,规则也就无法成其为——在实践意义上的——规则,而如果要强行维持规则我们也许又必须从语言逻辑重新折回到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