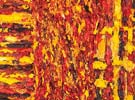Q.你何时在何地出生?
A.1956年10月,我出生在云南滇南方向的一个小城弥勒县,县城当时不超过一平公里,四面环山,东西南北河流如银蛇般游动,拥抱着呈半圆形凸起的小城所居地,似龙戏金珠。春里鱼欢雀跃,冬节山舞银蛇,野驶炊烟,夏节河岸栖柳,轻歌曼舞,秋天一片金黄,大雁横空。
Q.描述一下你居住的地方?
A.我的家在城南的半坡上(祖上留下的土木结构房,楼上楼下约120平米),视野开阔,站在楼上的阳台上能看见南面的旬溪河,左右伏卧着重的山背,及一眼看不尽的稻田,秋里能阵阵闻到稻田里传来的清香。当地的广播电台在我房角处装了一个高音喇叭,天刚亮那大喇叭口便拼命地大声吐着刺耳的歌及来自中共中央的各种指示,实在受不了时,手中的弹弓把石射进它的大嘴里。这一切早在30年前就一点一点地消失。如今生出了人造的湖,花花草草,河流还有那田野,却永远消失了。
县城四面环抱的山上,居住着十一个不同习俗,不同语言的少数民族,汉族人口与这些少数民族的人口比例几乎是1:1。他们聪明、善良、勤劳,且都能歌善舞,其中有享誉全球的“阿细跳月”。
Q.描述一下居住地的建筑,环境,氛围
A.这山村里的一切对我早期艺术的成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弥勒的建筑从过去到现在,是我见过的最没有特色情趣的建筑之一。可以说谈不上是建筑,过去是简易民居,如今的房子什么都不是。会造房子的是那些被大汉族在千年前就赶上山的当地少数民族,只是他们势单力薄被赶走了。他们的聪明才智被压缩到山里,所以如今的城市永远不如山里的民房好看。弥勒县属于基本没有象样的历史文化遗产的小城。没有博物馆,画廊是从未有过。有个图书馆,里面也仅仅只有一本中国传统绘画画谱。
Q.描述一下你的家庭
A.我的父母挺能生,先生了我,之后生了两个弟弟,两个妹妹,大弟弟刚生下没多少时日便饿死了,我死了几次,死不过去,死里逃生了。但复活注定是有代价有使命的。六岁开始便学烧火做饭,七岁身背第二个弟弟再做饭。十岁招呼弟弟背着妹妹再做饭。我如一只小驴,边长边加负重。
初中毕业那一年,刚进16岁,父亲挺不住,永远地倒下了。当下七十多岁穿着三寸金莲的祖母,一个月只能拿到七元人民币工资的母亲,九岁的弟弟,六岁和两岁的妹妹,中国人的俗规,“长子为父”,父亲原先负担的部分,长子承担。这头小驴身上又负重了,负重的驴儿在16岁那天开始在人生的路上跑了起来。
Q.你父亲是做什么工作的?
A.我父亲在他们那一代人中上了高中,算是读书出身,不幸的是他赶上了整治读书人的先头部队,1960年被从云南陆良县的邮政所发配到一个很远的林区去劳教伐木,更不幸的是他的腰被倒下的大树打折了,一天夜里几个汉子用木棒捆成的担架把他抬进家,全家老小除了哭什么也做不了。第二天祖母开始为他备草药,母亲给他上药,半年后他治过来了。分配到县里的一个工程队赶马车(工程队后来改名为建筑队),有趣的是到了八十年代,我被分流进这家建筑队,子承父业,还真是想躲也躲不脱。
Q.你父母鼓励你的创造力吗?
A.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从未显现点滴的艺术爱好或才华。仅见过他在有一年的春节,亲手用纸、竹纤、面糊做了一条比我高的鱼挂在门口。这是父亲给我及弟妹的唯一一件玩具。他没有笑过,时常满脸心事的样。
有一个晚上他去同工友们喝酒醉着回家,歪歪斜斜,母亲上前扶住,他面笑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觉得如此的可爱可亲。他手里递给母亲一个拳头大的缸,里面装了一些吃剩下的东西,嘴里重复着:老婆,你放心,我一定会把这几个娃娃养得胖嘟嘟的……
Q.你跟你的母亲很亲近吗?
A.母亲只上过一年的学,生性多愁善感,是中国典型的善良妇女,三岁前曾被强迫裹三寸金莲,后反抗逃跑。三寸金莲未能最后形成。父亲不哭也不笑,母亲的泪水却如小溪不停地流,有时是因为我的弟妹们被父亲暴打,有时不明白为什么哭,如今想真是满肚苦水,流不尽啊!那个时代苦难交加的中国妇女要么就哭,哭完了第二天哭日子接着过,要么就哭不出来,第二天投河跳井。
Q.孩提时代谁给你最大的灵感?
A.我的祖母是这个家庭里最了不起的人,从她的脸上看不到正经历着的苦,她总是面带微笑。青少年时代没上过学,五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创立了一些扫盲夜校,祖母上了扫盲班半年之后,一直自学到82岁离开人世为止。她在世时我们家总有亲朋来访,邻居上门来玩,很受人尊重,她遇事总是以理服人。父亲是读书人,我出生时给我取名罗旭,祖母不是读书人出身,给我取了个小名“天喜”,是个多么意味深长的小名,“天喜”。
祖母的书全是手抄书,有佛经(父亲死后祖母成了虔诚的佛教徒),中国古典名著,民间故事……她特别喜欢我,时常把我抱怀里,讲民间故事给我听,读佛经里关于善与恶的因果事迹,讲三国、水浒传英雄故事。
Q.你祖母跟你一起居住吗?
A.我三岁后祖母便陪着我在一张床上睡到14岁。这样祖母每个晚上老是要给我讲点什么,13岁后我有了自己的床。其实我的学前学间教育得于我那从未上过学的祖母,而非读书人出身的父亲。六岁祖母便手把手教我生火做饭,七岁便跟随邻居家的比我大一点的小孩到离家七八公里的山上去担柴,八岁后已经可以到田间去割青草卖给马夫;当时父亲的工资9元人民币,母亲7元,我十岁后每月担柴割草卖的收入超过父亲,在那个年龄里没有苦的感觉,我喜欢田野,在青青的麦浪里和鸟一起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