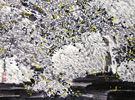我的态度始终是现实主义的
《画廊》:我们看你的创作历程,步骤是非常清晰的,比如说“光头”,先是单色的,后是彩色的,之后又加入了“水”的因素,有一个冷静的通盘的思路,而不是像有些艺术家那样循着自己的激情进行跳跃性的创作。你是否有对一个符号细心经营的考虑?
方:首先我认为理解一幅作品,不能独立地看,它有它的独立性,但不是百分之百的,它肯定有上下文、承前启后的这种关系,同时也是受这种关系决定的。所以我对自己作品的控制不太拘泥于一幅作品是否非常好。如果你做的别人说是最完美的,那就不值得再去做了,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失败。你可能在单件事情上是完美的,但是在上下关系中却是一个死局,这样就不好了。
《画廊》:你是在力求保持创作上的一种动态演变的关系。
方:另外,这种发展变化有人为的因素,但是这种人为的因素对其发展的脉络能占多大的比例还不好说。我们打一个贴切的比方,这么些年来你作品发展的过程,它很像一个小孩,一开始在摇篮里,慢慢地可以坐起来、可以爬、可以扶着慢慢地走,最后可以跑,变成刘翔那样。这个发展过程是人对自我的认识、是一个建立自己自信心的过程。
《画廊》:从画面的图式来看,大家惊奇地发现你近期的作品有了很大的变化,像裸体婴孩、苍蝇、蜜蜂、飞鸟等形象的出现,以及密密麻麻的小动物呈放射状分布的构图,这些新特征有什么来源吗?
方:其实人的立场就和相机的镜头一样,有时是微焦的,有时是自拍的。我觉得可能也受到中国传统的影响,我其实是想表达众生平等的理想概念:在画面里我画了一些不吉祥的动物,像苍蝇,也有一些可爱的动物,这与年画可能有关系。其实在人群当中也是这样的,我们会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好的坏的、不同工种的?? 但中国大部分人又都受众生平等的观念影响。另外一个就是说,你站的位置不同,你很贴近的时候,会清醒地知道你是一个人,但是稍微远一点,你是没有办法把人当成人的,你可能还不如画面里的一只苍蝇和蚊子那么重要。
《画廊》:我看到你一些雕塑的手脚连在一块、表情怪异的卑微形象,并且在布置展览的时候还特意将这些雕塑置于不起眼的角落,这包含着你对人的生存处境的一种什么看法?
方:我一直认为自己是现实主义的。可能有些作品是漫画化的、有些作品是理想化的,还有一些是放大的,但我的态度始终是现实主义的。所谓的现实主义态度就是,我不拘泥于一个现实主义的场景,我是想通过画面构建起人和人、人和理想或者人和自然的世界关系。我们都知道造型艺术有具体的形状,往往容易卖弄技术,把重点放在了所谓的现实主义的场景中,我们几乎很少能够通过具体形象去揣摩其与现实主义的关系。至于这些趴在地上的雕塑,我认为是写实的,因为在现实生活里面,在我们的社会背景和现实关系之中,一个人的位置可能有差价感。这些作品再怎么说,毕竟发表了,被人注意了,被人关注,甚至可以卖钱,这一切都比原生的生命更重要了。我曾写过一段文字,我的理解是,其实我们真实的生命可能就像尘埃一样,不被人注意和关心,没人知道,但是我没有办法去描绘尘埃,所以我们对任何人的表现都有夸大的成分。
《画廊》:画面形象的转变可能也蕴涵着你个人视角的变化——从将芸芸众生中提取形象鲜明地凸显出来到对微小个体的平和观照。
方:这种变化有很多的因素,首先跟年龄和经历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