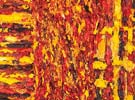这需要做出三重身份,三重“话语”之间的比较。过去的石鲁艺术研究者只关注他们感兴趣的,也就是与他们自己的文化身份相称的那一部分“话语”,这就是只能走向片面的认识。有幸在此世纪之末回顾往事,我们可以比较轻松的毋用避讳的游弋在历史的各种“话语”情境中,了解那时的人们何以不识庐山真面目。从这种意义上讲,《石鲁文集》的主要价值就在于以一种历史档案的经验性提供给我们一些当代思考的张力支点。因为我们不可以幻想,我们已经完全改观了历史情境,某些历史“话语”的余韵犹在耳边缭绕,或依然在无意识中左右着当代人的某些文化习性。
“话语”是个什么东西?作为有言语能力的高级动物,有语言修养的文明人,我们却只能具体的生存在一个个“话语圈”里,我们总在讲着某类流行的“话语”或者权威的“话语”,其中的语义是特定的,逻辑是预置的,价值判断是严格规范的。特别在一个权威思想统领一切的社会型态中,遵从“话语”的规则是一个人能否好好活着的首要条件,如果你想在公众事业上有所作为,你更须把权威“话语”彻底植入脑神经之中。你自己消失了不打紧,你已经成为“话语”中人才是可喜可贺之事。
“话语”在权威——公众化层面上是一个强大的定势思维系统,它显而易见的好处是具有惊人的集体感染力和凝聚力,它隐蔽的坏处则是单调划一,僵硬乏味,帝国过份的夸张而招致“物极必反”;“话语”在个人意义上是自在的沉思遐想,它有许多萌发生机的可能,也常常在无效的自言自语中埋没。当一个人扬弃一种“话语”而投身另一种“话语”,是为思想觉到了困顿而欲更迭,生命力呈现出活跃,逆反,不再安份守已的亢奋状,亦为可喜可贺之事。
一
五十年代石鲁的学术文章,更多的像是宣传工作报告。从抗日战争,解放区的保卫战,土地改革的斗争会传袭下来的军事共产主义体制,由此产生的文艺应该完全围绕政治中心任务,鼓动干部群众政治热情的社会需要,造就了势倾一切的“政治宣传与文化普及的话语”。石鲁做为新晋的西北地区美术界主要宫员,也由于发自内心的革命理想主义信念,他既有责任也有激情的全身心投入到这个“话语”系统中。他毫不含糊地说:“劳动人民做了画中的主人,政治思想成为美术作品的灵魂……,美术只有为人发服务,才有价值,才有作用;美术只有反映现实才有生气,才有发展。”(《如何开展西北的人民美术运动》)他呼吁:“人民在文化上迫切的等待着充饥的粮食,而不允许我们慢条斯理地做精细的小锅饭,……我们的美术工作者如果在思想上,立场上以人民的思想为思想,以人民的需要为需要的话,我们就必须重视大量的普及的东西,坚持普及第一。” (《如何开展西北的人民美术运动》)他严厉的指责:“在某些作者思想深入仍有‘唯艺术至上’的遗毒在作祟,个人的偏爱和兴趣常是这种腐朽思想的最舒适的温床。他不了解作为人民和美术工作者,在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上,应当从人民出发又以人民为归依,不是自己站在提高的凳子上,随便给‘普及’一点黑面包皮。”(《年画创作检讨》)石鲁不仅是这个“话语”系统的报告人,也是实践者,五十年代他创作了版画《打倒封建》、《说理》,表现了阶级斗争的政治主题;创作了年画《幸福婚姻》、《巧女绣花山》,是对农村新风俗新生活的讴歌;创作了彩墨水画《王同志来了》、《古长城外》等少数民族题材作品,宣传国家的民族政策的成功;创作了水墨画《背矿》、《击鼓夜战》,是对声势浩大的“大跃进”的赞诵。
五十年代后期,石鲁也开始思考另一类“话语”——对中国传统民族艺术形式的再评估。其缘由来自一种争议,在“政治宣传与文化普及的话语”主导一切之时,传统民族艺术形式被划入封建主义文化范畴,被认为不适宜为社会主义服务。那时,鼓动“全盘苏化”成为时尚,“把油画奉为最科学的,最先进的,最高级的世界性艺术形式”,而中国画则成为落后过时的老古董。1958年石鲁写了一篇措词极为激烈的文章“为什么要继承与发展民族优秀传统”在《美术研究》上发表,矛头直指全国美术界的主要领导人江平,他认为江平是否定中国传统艺术的代表。在这篇文章里,石鲁主要是论证中国传统绘画的艺术性与科学性问题,批评江平代表的“民族虚无主义”观点,本来这应该是一种正常的中西艺术比较的学术之争,但石鲁给文章所加的副标题“——批判江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令学术问题充满了政治斗争的火药味,文章中大量的政治斗争“话语”给艺术性和科学性论点蒙上了一层阴沉的色调。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江平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定为右派,他的思想倾向和历史公案不是本文的话题,我所深感遗憾的是那时的石鲁在不同的“话语”系统之间的迷失。艺术问题政治化,是那个时代的流行病,弄得人人发烧,动辄以意识形态的武器互相攻击,权威“话语”中人石鲁,当然逃脱不了这种局限。然而仅仅五、六年之后,同样的“话语”怪圈就反套在石鲁头上,石鲁的艺术创新遭到了政治“话语”的猛烈攻击,八年之后,石鲁就在“文化大革命”的战鼓声中被打入“反党反社会主义文艺路线”的另册,历史的反讽何其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