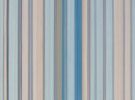吕植:一会大家对王博士讲的这些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有时间来讨论,那么下面呢,是给两位张博士,刚才王博士谈的是对我们国家目前面临的气候变化的状况、和未来大家纷纷谈的承诺。作为地球公民,我们每个人在这个地球上生活,都有自己排放的碳足迹,大家都有意愿减少碳排放,但是同时又有发展的需求,就是刚才田松博士也争论的这个需求,这到底是一个真实的需求、还是我们臆造出来的需求? 就是说,要发展,发达国家已经发展了,那么我们发展中国家也有权利享受发达国家已经享受过的这种物质文明。 这是另一个话题,我们先暂且不论这个逻辑有多大程度是对的,如果这个说法是个现实的话,刚才王博士展示的这个未来的排放的情景,就是所有的发展都是和这个排放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要改变,把这个温度控制在两度以内,这个两度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八国集团开会时候发达国家承诺的,那么,我们全国人大也通过了这个说法,我们也要赞成把温度控制在两度这个温度的上限,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全球的排放上限。 至于在这个上限下面,发达国家怎么排,发展中国家怎么排,谁先排,谁后排,什么时间达到什么样的峰值,这可能是现在好多谈判的一个细节,但是无论如何,大家在谈一个上限,我们全球的排放必须要有一个上限,至于这个上限,是2度,2.5度,还是哪一年达到这个度,确实是有一个幅度,那么面对这个上限,实际上对我们每个人都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要减排。那么,减排这件事情,究竟可能不可能呢,我很想听听两位张博士的看法。在中国来讲,在这个前提之下,在这个情景这下,比如说,假设你是一个中国的企业,你会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张冀强:我首先感谢山水把我邀请参加这样一个很不寻常的会。说老实话,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不自在的会,因为环境对我们是一个专业,我们经常跟专业人士打交道,跟艺术家、文学家、企业家打交道对我们来说是一件新鲜事,所以感到不知道怎么办好。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但是有一件事,我想是顺便有感而发吧,就是环境作为一个专业现象,如果要逐步过渡成文化现象的话,事情可能就不同了。在西方国家,在美国,大概至少有25%的人是执着的环境主义者,只有25%;另外还有25%的人是执着的非环境主义者,那么其他人都是中间的。欧洲的执着的环境主义者大概有40%,美国人这样描绘环境主义,他们认为环境主义是一种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呢,实际上是一种客厅文化,反环境主义者认为,你们就是端着红酒,坐在客厅里,谈着原始文化有多么美好,我们说到原始生活状态的那些非洲同胞,或者我们某些少数民族也希望你坐在他们的客厅里,把你请到他的村子里去坐着,他谈论着你的生活多么美好。这是一种说法。不管怎么说,我现在想说的就是说,环境现象如果能转化为一种文化现象,能达到25%或者40%的时候,我们再谈论环境问题的时候,情况就会很大的不同。但是并没有解决问题,就是刚才所说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回答,所以还请诸位今后好好的思考这件事,因为这么多有哲学思想的人,希望你们能想出一个答案来,我是没有。
但是我想接着刚才这个话题,吕博士提出来的这个问题说,就是减排承诺有没有可能?完全是有可能的。当然这里都有很多矛盾的地方,没有一个固定的,绝对不错的答案,这是没有的。首先,气候变化问题,从一个专业人员的专业问题,逐步现在变成了政治问题,现在气候变化还会变成文化问题。我认为,这个政治讨论实际上是一种扭曲的政治讨论,是过度政治化的讨论。把气候变化问题政治化,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现象。具体是什么现象呢?就是:发达国家说,我们承认我们的历史义务和我们现有的技术资源及财政资源,所以我们承诺优先减排,但发展中国家也要减排。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它承诺减排必须拉着中国政府作出环境、气候变化方面的承诺,否则,另外反环境的25%就饶不了它,下次选举它就会被排斥。所以对它来说,最好中国政府能作一些让步,这样的话,它才能做更多的工作。这个理论本身并没有错,但是如果谈中国和美国,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当中则有一个很重要的误区:像中国、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有60%至70%,甚至80%以上的农民。若中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是美国的四分之一,那在座各位和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就可能非常接近美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如果不是二分之一,可能就是四分之三、五分之四。特别是开车来的同志,跟他们基本相同。如果你家里有空调,如果你每天洗澡,如果你开车上班,那跟美国人没什么两样。所以,我们中国之所以有四分之一这个数字,是因为很多人不洗澡,或者一个月一次,甚至一辈子只洗两次澡;是因为他们不开车;因为他们用牛粪、用柴火来做饭。这些是形成四分之一的原因。倘若我们现在承诺不增排,那这些人是否永远都要用牛粪、用柴火来烧饭?是不是就没有资格吹电风扇、吹空调?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即使在国际谈判桌上,发达国家也不会说,中国的西藏人民只能用牛粪烧饭,不许用天然气,也不许用其他的化石燃料。我认为,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帮助那些能源消耗很低的人群的。在当今社会,那些人群依然占大多数。我不知道具体的数字,我们有个课题正在调查这个事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数字非常之大,按照联合国的标准,至少有一亿多人民处在贫困线以下。实际上,生活在贫困线一下、能源消耗很低的人可能不止一个多亿,有好几个亿。如果把印度、非洲国家加上,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人群。如果这个人群的生活状态得不到改善,谈减排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在谈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谈到减排和能效的时候,必须认识到我们是不一样的情况,不一样的社会。我们要对那些人群提供有效的清洁能源技术,提供有效的新的消费模式。至于这个消费模式是什么,我们还不知道,但我们正在创造。我们组织一批人研究农村能源问题,我们在研究如何改善农村生活水平的同时,又不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甚至有一个可能性,我们可以做到负碳农业,碳排放是负的。这是完全可能的。最近两三年以来,有一个潮流,就是把农村的秸秆、农业废物、甚至是牲畜的粪变成燃料的同时,生产出生物炭。大概有百分之四十的生物质可以变成生物炭。生物炭如果还到田里,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储碳的方式,我们称其为CCS,就是碳捕捉和存储方式。这种方式,能通过农作物的光合作用,把二氧化碳吸附在植物身上。粮食和农产品被我们消耗了,但40%的剩余物质可以还到田里,达到储碳的效果,而且这种生物炭还可以增加土壤肥力、提高土壤生产力。目前研究表明,生物炭如果施加到田里,在最好的情况下,可以使作物的产量提高三分之一到百分之五十,并且可以减少化肥的使用。
吕植:谢谢张博士。刚才王博士展示的曲线,说明发达国家的排放量还没有达到峰值。张博士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提醒。中国最需要帮助的人口,是农村人口。他们仍然需要发展,需要享受物质文明。他们的发展是否能成为一种先进的低碳排放的发展?排放与发展能否脱离?以前我们说发展中国家有发展权,是把发展与排放联系在一起的。而张博士让我们认识到,排放与发展是可以脱离的,起码二者相关程度可以降低。我们常说到经济发展的拐点,就是可持续发展是不是总需要高消耗、高排放达到社会的物质积累后,才能回过头来关注社会环境?张博士刚才说到的前景,虽然需要我们花很大的精力来推动,可他证明了这个曲线并非不可避免。在我们气候变化的讨论中,涉及了很多的话题。不仅说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博弈,贫困人口和富裕人口之间公平性的问题,同时也涉及了国家和国家之间,或者是各个经济实体都面临的排放的问题。我们刚才第一节谈论到人类发展的诉求在经历什么样的过程,现在我们说人类的发展是要付出代价的是什么,比如说气候变化。这些代价需要全人类来承担,但具体谁承担多少,是我们谈论的问题。现在有一个问题,我想听听张建宇博士的看法。如果你关心气候变化的话题,或者你关心新闻,那你就会知道,前不久,美国发布了一个能源安全和气候法案,又称为Waxman Bill。在这个法案里,我们中国关注最多的是一个词:碳关税。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在目前我们与美国如此大量贸易的情况下,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会有什么影响?希望张建宇博士给我们解答一下。
张建宇:非常感谢。大家可能不知道,我跟吕教授认识很长时间了。接到邀请到这儿来讲话,心里还是很忐忑不安的。因为虽然我做了很长时间的环保工作,但吕教授经常批评我,说我对自然没感情。他们都是对自然很有感情的。对自然没感情的人,和对自然充满感情的人说话,自然有点忐忑不安。刚才听到上一节介绍时,有个地方让我特别有感触。说明我的感情。
刚才在地下室的展览中,说到地球上将失去的几十种声。这肯定是非常遗憾的。因为有些声音我们还没有听到就消失了,或者即使我们能听到,那只是录音,而不是实际发出的。有件事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但我是很关心的,因为我是满族人,就生在故宫旁边,对满族很有感情。去年,随着辽宁省满族自治县一位一百多岁老人的去世,会说满语的人再也没有了。满语作为一种语言,文字还有保留,但作为一种人文现象,作为一种曾被大家使用的语言,它消失了,它的发音无法流传下去。现在,可能还有人会写满语,在偏僻的学校角落里还有人在学习满语,但世界上再也没有会说满语的人了。这实际说明了一个问题,是我们关心环境、关心地球的另一面,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们今天并不能把它说清楚。我们把由来的自然、我们自己还有的、以及我们将归去的自然,这三者究竟放在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到底应该保护什么?我们应该把什么放在最主要的位置上?我们对人的关心有多少?在我们做所有的决策时,我们应该把对自己的关心和保护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值得大家重视和思考的问题。
刚才是一点感触,下面谈几个技术问题。大家可能都不是特别关心,但既然吕教授请我来,我觉得还可以谈一下。第一个是升温两度的问题,刚才王博士也给大家介绍了,这非常重要。两度的问题不仅是发达国家要承受的问题,实际上G8、G5发出的一个联合声明中,对两度问题进行了认可。这个声明,如果大家去查原文的话,用的还是aspirational (意向性的), 对于搞气候变化的人来说,至少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为什么这样说呢?不管我们对两度问题有没有争论,但在联合声明中,所有的最大的发展国家、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已经承诺到2050年,要把气候变化控制在pre-industrialization的两度范围之内,尽管用的是aspirational这个词。因为在这之前,我们世界在看待气候变化的问题上,用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oversimplify (过度简单) 的解释来描述,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就是说,大家处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有的国家还要增加,有的还要下降;有的国家就算你不去控制,因为人口问题、技术更新,它也会下降,有的会增加一段时间然后再下降。自下而上就是说,大家看着来,遵循你自己发展的节奏,根据你发展的过程,找出适合你自己的发展道路。我们大家加在一起,世界能走到哪就到哪,不会后悔,因为我们都努力了。关于G8、G5为什么在六月底把两度写到联合声明中,里面有很多政治的博弈,我们不去考虑。我觉得,它说出两度问题,就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为什么?因为从此之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至少在自下而上的角度中会夹杂着一点自上而下。自上而下就是说,我们要以结果为导向,到2050年实现控制目标。那么我们一共要排多少吨?大家可以算一下,发达国家能排多少发展中国家能排多少,要开始算账了。虽然这个算账,包括大家很关心的国际谈判,有很多个角度、很多博弈的问题,但我觉得从自上而下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以结果为导向,应该说是我们在控制思路上的一个很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