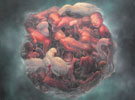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笔者以为,从“思想激情”到“伦理责任”,直至“道德理性”,虽然历史与当代艺术之间不乏悖谬与张力,但这样一种吊诡性存在的确是一个去意识形态化的政治生成。因而,作为一种以记忆抵抗遗忘的方式,当代艺术在此绝非仅只是一种简单的反抗姿态和对立立场的标明,毋宁说,它意在以一种更理性、更冷静、更审慎的心态看待这一抵抗,包括妥协。易言之,如果说遗忘是一种非自觉的行为的话,那么记忆是一种自觉,甚至是一种判断,一种选择。这一点,亦为李公明尤其强调,他说:“与当代艺术景观中常见的对历史图像、符号的挪用者有着根本的区别是,本展览倡言历史题材创作的本体属性:对历史题材的选择、价值判断、表现形式的创造、作品表达的完整性等等。”问题就在于,选择是基于某一“道德理性”,而被选择的历史(真相)本身也涵有某一“道德理性”。且在更多的时候,这两种道德理性之间恰恰是相冲突的。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此基础上再次做出选择。可是,这一选择又依凭于什么呢?
近一百年前,韦伯念兹在兹也正是这一点。在他看来,对于有权参与转动历史车轮的人来说,需具有三个决定性因素:“激情、责任和眼光”。因而,仅只“思想激情”是不够的,加上“伦理责任”也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眼光”、需要“洞见”(insight)。换言之,对于今天的我们——不论是艺术家,还是批评家——来说,缺乏的不仅是“思想激情”和“伦理责任”,还有“眼光”与“洞见”。而韦伯的思想实践也足以证明,抵抗遗忘、重构历史还需要“眼光”。不过,韦伯虽然洞悉了“激情”“责任”及“眼光”,可是,他忽视了人类、历史向度上的“德性”或“道德理性”。正因如此,他的关怀也仅只限于民族、国家视野之内。而这也是其为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所诟病的原因所在。
当然,不论是对于艺术家,还是对于批评家,体验与“洞见”还是其实践的基本支点。不同在于,对于艺术家而言,自然基于个体生命意志的“思想激情”更为重要,而对于批评家而言,则恰恰相反,人类与历史向度上的“道德理性”则优先于“责任伦理”与“思想激情”。易言之,哪个优先,哪个则为切入点或出发点。于此我们不妨图示为:
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到艺术创作与批评之间的张力所在。如果说个体的“体验”与“洞见”是二者共同的基本支点的话,那么基于社会层面上的“责任伦理”乃二者共同的关怀与实践对象,显然,“洞见”实际上正是源自个体于社会的体验。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其反证了这实际上就是作为策展人和批评家的李公明、胡斌的展览。
余论:“当代历史创作”与自我认同
正如策展人胡斌所说的,其就是在艺术界对主流美术与当代艺术两个“江湖”之一不断的今天,寻找另一种可能。显然,他所谓的“当代历史创作”并非今日官方所提倡的国家意识形态控制范围内的艺术创作,也不是简单地以反对或抵抗国家意识形态控制为名义的创作。其既非站在外部视野,也没有站在内部视野,而是选择了一种整体视野。也就是说,两位策展人所谓的“当代历史创作”已然超越了简单的意识形态限定,而建构了一种新的自我认同。换言之,它既包括了外在视野中的中国认同,也内涵着基于内在视野的个体认同。因为,在这里历史本身便已超越了国家与个体之争。
表面看上去,这样的展览是没有立场的。我想,李公明之所以没有标明某个姿态,也正是因为历史及历史本身的复杂性。特别是在面对诸多重大历史事件,试图以一个简单的立场揭示真相时,或许那反而是对真相的遮蔽。历史其实最怕立场。这一点,我们从展览的作品也可以看出,艺术家们对于历史的态度绝非是单一的,更不是以对立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姿态出现,反之,它呈现了多个面向,有的甚至契合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观。而李公明所主张的也正是这样一种对历史的自由表达的权利和态度。当然,自由并不意味着随意书写,自由更是一种责任,一种道德。因此,如果说李公明先生有立场的话,那么这个立场就是“责任伦理”,就是“道德理性”。亦如前面所言,在李公明看来,作为记忆,艺术是抵抗遗忘的一种方式。显然,作为记忆,艺术更像是一种私人的行为,而作为一种抵抗遗忘的方式,其所指的似乎还不仅只是个体,而潜在地被赋予了某种历史的担当,集体的责任。
可见,这是一个去立场化的立场。而这样一个立场也决定了,其并非是国家与个体的同时认同,更非依寓于自上而下——即从国家到个体——的自我认同,而是基于自下而上的从个体到国家的一种认同。所以,李公明真正追问的是历史中的个体命运,包括历史为什么会被现实中的个体所遗忘,这些都是他的考量对象。殊不知,正是这样的追问将认同从个体引向了家国,从内部视野自觉地延伸到了外在视野,引向了人类及其历史。很多历史重大事件发生及其被历史所不断重构其实就是源于这里。由此,我们需要更进一步地追问:为什么这些重大事件会被不断地重构?内在之外,就一无所有了吗?我们该如何面对自我历史被他者曲解的情形?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个“坏世界”及其国家、文明之间的“丛林法则”呢?毋庸置疑,正是这样一个复杂的现实与历史背景决定了这样一种充满吊诡的认同自觉,对李公明、胡斌而言就是一种使命。